哲学月|第二十四届哲学月智慧之光名师讲座系列 第四讲顺利举行
2021年11月18日上午9时,时值第二十届世界哲学日,哲学系第二十四届哲学月“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名师讲座系列第四讲正式开始。本讲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黄勇教授,我系李长春副教授与陈乔见教授分别为主持人与评论人。讲座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方式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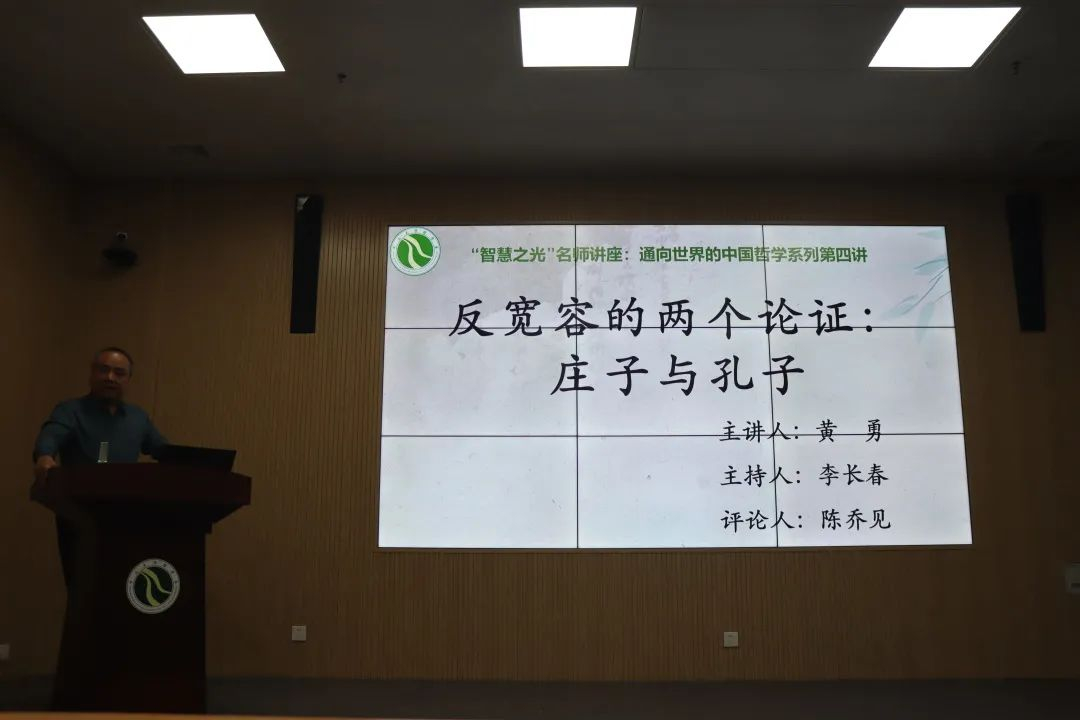
黄勇教授的讲题为“反宽容的两个论证:庄子与孔子”,旨在从中国哲学的视域探讨和反思如今世界上广泛认同的“宽容”(Toleration)价值。黄教授首先介绍了西方历史上宽容观念的发展,特别是洛克、密尔和罗尔斯的相关论述,直至联合国将1995定为宽容年,并将此后每年的11月16日定为宽容日。黄教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表述为例,说明当今宽容的用法主要系针对异教的、种族的、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流动工作者、外来移民或难民、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等;而他将表明宽容在此完全是不恰当的。
黄教授从“宽容”概念入手分析,他说西方学界对宽容的标准定义包含三个成分:
(1)反对成分(objection component),意谓被宽容者被认为在重要的意义上是错的或坏的;(2)接受成分(acceptance component),意谓在不取消对被宽容者的否定性判断的前提上,给出特定的理由以胜过否定的理由,从而可以接受或容忍被宽容者;
(3)拒绝的成分(rejection component),意谓宽容总是有个限度,宽容的界限需要被明确界定,这个临界点就在拒绝的理由胜过接受的理由。 黄教授援引西方学者的分析指出,与此三个成分相对应,存在者三个宽容悖论:
(1)种族主义者悖论,即种族主义者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值得平等尊重的所谓“劣等”种族要更加宽容,如此,他们这种不道德的态度似乎反而成为了一种美德;
(2)如果拒绝和接受的理由都被称为是“道德的”,那么,似乎道德上对的甚至是道德上要求去做的就是道德上错的那些事物。
(3)划界的悖论,比如我们会认为那些不宽容者不需要或不能够被宽容。
在黄教授看来,在“纯粹反对”(pure objection)和“纯粹接受”(pure acceptance)的两种情形中,“宽容”都是不恰当的;宽容只适用于“伴随反对的接受”(acceptance with objection)的情形中。黄教授认为,一方面,在那些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加以反对的情形中,对待那些不同文化或伦理的他者或差异者,宽容是不恰的,我们应该像庄子那样承认他者文化样式的合理性。在此情形中,需要的不是宽容而是尊重。另一方面,在那些我们有很好地理由加以反对的情形中,宽容同样是不恰当的,正如孔子主张“以直报怨”“正曲为直”那样,在此需要的不是宽容而是矫正或教育。总之,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主张宽容实际上具有某种危险性,它很有可能会强化偏见。
综上,黄勇教授的基本看法是,宽容与不宽容看似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它们有一致之处,即都暗含了被宽容者是错的或坏的,区别仅在于能否忍住不去干涉。黄教授认为,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充分表明,“宽容”既不是一种价值,也不是一种美德。
讲座的最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分别向黄勇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李长春副教授提到,反对意见是否基于更深的原因,比如自然差异或文化差异。陈乔见教授在评论中认为,要理解黄勇教授为什么反宽容,关键在于理解西方宽容概念所含有的“反对成分”。为此,他扼要重述了西方“宽容”概念的三要素。他赞同黄勇教授的看法,认为宽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中的用法的确是不恰当的,但他认为这会不会是作为哲学家所讨论的严格意义上的“宽容”概念和日常用语中的宽容用法之间可能存在着有差别。陈立胜教授指出儒道两家实际上有着与西方“宽容”概念不一样的“宽”“容”思想,值得阐发。此外,现场和线上的听众也提出不少问题。黄勇教授皆一一耐心作答,展现了哲学思辨的独特韵味。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