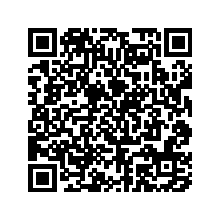“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八讲 | 侯猛:作为理解中国的“政法”
侯猛:作为理解中国的“政法”

雨生百谷,“政法”开讲。
2024年4月22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八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如期举行,本讲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侯猛教授主讲,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吴重庆主持。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肖滨教授也出席了本场讲座。羊城谷雨惊雷纷纷,入穗航班大多取消,本次讲座不得已采取线上方式举行。

“标识性概念首讲‘人民’,这一讲又来到了‘政法’,我们对标识性概念的认识不仅从中国悠久的传统与文化入手,还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出发……我们的‘公检法司’前都有‘人民’二字,充分体现了‘政法’概念的独特内涵。”吴重庆教授开篇主持便引入了“政法”概念讲座的设想由来,随即侯猛教授以极具人民共和国年代感的逐浪马列大楷体标题开启了讲座内容。
一 “政法”:作为理解中国的标识性概念
侯猛教授以“说词”“说事”“古今”与“中外”四个角度探讨了作为理解中国的“政法”标识性概念。侯猛教授首先以南洋公学与北洋公学的设置为引,探讨了“政法”与相近概念“法政”背后的相异法律观。
鸦片战争后,有“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称号的盛宣怀上书清廷设置北洋公学(今天津大学前身),以练工科人才产业救国,设置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以练法政人才思想救国,尤其是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重建政治制度。彼时盛行各省的“法政学堂”之“法政”一词很有可能来自于日本,就如“权力(利)”“法理”来源于日本一样。
不过,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政”不同,“政法”并非是效仿西学的结果,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重建新法统,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政法”概念的背后,是马列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作为支撑,而“法政”则是自由主义的法律观作为支撑。因此,“政法”就构词而言,是政治法律的简称,而非政治与法律的简称。单以“政治”或“法律”包括“法制”都无法理解中国,“政法”一词恰好有助于理解中国。为此,侯猛教授还以1949年《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的文件精神作为典例。
侯猛教授言毕“政法”一词后,顺势考察“政法”所指之事。首先是溯源“政法”一词的使用起点。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公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简称《大事记》)中,“政法”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表述中,即“在起义中,总指挥部设立政治保卫处,作为人民军队政法保卫工作机构。”此处的“政治保卫处”就相当于如今的公安部门,因此,“政法”所指之事最早可追溯到公安的起源。
在《大事记》中,“政法”一词第二次出现在1928年5月20日-22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上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军事、财政、政法等部。与1927年“政法”一词相比,1928年出现的“政法”是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作为基础建立政权后,实行法律、创建法制,因而具有标志性意义。有一种说法认为,官方开始广泛运用“政法”一词是从1949年开始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了有“北朝阳、南东吴”之称的朝阳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其“政法”校名大概来源于贾潜的提议。虽然其后以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二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以第三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央政法干校,但“政法”一词也被五所新成立的政法院校所采用。不过,最近发现了更早的文献资料,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政法”一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例如,1946年边区三届参议会通过之提案中有“政法组”之说法,这表明在参议会成立的1939年,“政法”一词可能已经开始使用了。
具体到内容而言,2020年,侯猛教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新中国政法话语的流变》一文,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政法”所指之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法工作范围十分广泛。除了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以外,也包括民政、立法、民族和监察事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政、立法、民族和监察事务逐渐从政法工作中剥离出去。简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法概念所指之事始终未变的就是审判、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和监狱。这也与《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三条所规定的政法单位一一对应,即主要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而民族、监察、立法、民政事务早先属于政法事务,但后来逐渐剥离,因此不再被认为是“政法”的核心范畴。
“政法”概念的古今对比,也是侯猛教授关注的对象。毛泽东在《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句话,即“百年皆行秦政法”,侯猛教授认为此处“政法”同现代“政法”本质不同。传统“政法”与“礼法”“儒法”以及“宗法”本质更接近。现代、传统“政法”相同之处在于都较为强调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与身份。
与传统社会强调尊卑有序不同,现代“政法”所强调的身份是“敌我关系”,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询问一样,即使在当今政法工作以及《政法工作条例》中,也仍然强调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敌我的区分”其实是“政法”概念如今的身份色彩。“政法”概念也有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也有社会规范即2014年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法治体系中的“党内法规”。
在事关“政法”作为标识性概念的中外交流问题上,侯猛教授比较了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以及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的语言表征。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和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都是来自于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习近平论依法治国》英译本中“政法”概念的有关翻译,前者(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用于“政法委员会”的翻译上,后者(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常见于政法单位(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Bodies)、政法工作(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Work)政法官员(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es)的翻译上。侯猛教授认为,“政法”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翻译为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便于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
二 “政法”:作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开宗明义,侯猛教授认为现在的“政法”概念还未能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并从政法法学、法学概念与法律概念、法律中的政法关键词以及从政法到法治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政法目前还不是法学学科意义上的标识性概念,但在法学的学术研究中,侯猛教授认为政法法学已经成为法学概念。这得益于朱苏力教授的贡献。朱苏力教授将法学研究的流派(格局)分为三部分,即政法法学、法释义学即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在他发表于2001年第3期《比较法学研究》的《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一文中,朱苏力教授认为政法法学的发展是自1978年至整个80年代并在某种程度一直延续。为了确立法学的自主地位,需要在政治上论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这种法学话语批判了极左的政治话语,讨论了法律和法治的一些核心概念,其思想理论资源基本上是广义的法学(包括政治学),其中包括从孟德斯鸠、洛克、卢梭、马克思、美国联邦党人等甚至包括后来的韦伯的理论、现代化理论等。这些思想资源并不是近代意义上强调法律职业性的法律思想。简言之,政法法学的功能,是在于批判极左的政治话语,以确立法律话语的正当性。
侯猛教授由此引申指出,政法法学一开始就是指代古典的政治法律研究。此外,在目前国内有关政法的法学研究中,还有国家法学,其重要的理论资源来源于卡尔·施密特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来自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学思潮。国内批判法学代表性人物是冯象教授,但他借助批判法学的传统,批判的是当下中国的异化的法学思想。国内批判法学的另一个代表是强世功教授,他是目前在主流法学研究中最有标识性持有批判法学立场的学者,并且整合了美国传统的批判法学同德国施密特以来的国家法学。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文本的研究,以及侯猛教授本人正在从事的政法的经验研究。而对政法进行经验研究就归属于社科法学的领域。
“政法”不是法学的标识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是法律的标识性概念。侯猛教授通过检索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时发现,“政法”作为独立的词仅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第二十八条,即担任人民警察领导职务的人员需要“具有政法工作经验”。“政法”说到底是党内的政治话语、政治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但政治话语与法律话语并非完全不兼容。重要的政治话语已经转变为法律话语,因此法律中的政法关键词就值得考察。侯猛教授以现行宪法为例,分析了数个政法关键词,并简要探讨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公有制”“劳动”“妇女”“法检公”等政法关键词含义变化的历史进程。
侯猛教授提醒道,从政法迈向法治,不是政法话语的使用减少问题,而是在公开表述和对外宣传更多提及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等法治话语。“法治”在中央编译局的使用上是Rule of law,同英语世界的使用没有区别。从八二宪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办案开始,再到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党的报告、文件并纳入宪法,以及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都在表明政法的内涵或者所要表征的内容与时俱进。从法检公到法治再到人权,这些变化是对过去政法工作的反思与推进,这也让政法迈向法治成为一种可能。
此外,具有里程碑式的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文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是其中提出“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赋予了当代中国法治(法治体系)更为丰富的内涵。
就此而言,政法就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法律观;第二是建政,包括夺取政权,建国以后建立基层政权,各级要建立人大;第三是社会稳定,这在两项重要的政法工作得以体现,即“平安中国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建设”在先是因为从建政到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 结 语
在结语部分,侯猛教授首先以强世功教授为青年学者邵六益《政法传统研究:理论、方法与议题》一书所写的代序《思考政法》展开。侯猛教授赞同强世功教授有关“小政法”与“大政法”的二分法,不过他也指出,强世功教授的“大政法”是指政治与法律,其言下目的是展开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同西方在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意义上进行比较的问题,但这终究没有脱离古典传统的政治与法律的讨论。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小政法与大政法,不是一般地研究政治与法律。小政法是研究公、检、法、司、国安甚至与监委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各个政法机关关系的讨论时,对政法或者党的意识形态、社会规范的关注,就如关注政法队伍整顿时对利用党纪要求整顿的分析。大政法的讨论则是党领导法治关系的讨论,即党如何领导立法、支持司法以及守法的讨论,实质上是如何全面依法治国的讨论。
其次,侯猛教授强调要通过理解政法工作机制、体制和传统,重新思考中国法体系和法秩序。今日中国之法体系和法秩序的讨论较偏重于法律规范或者是法释义学、法教义学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同当下的政法实践是相脱离的,甚至是刻意或不经意回避政法实践。这实际上就造成了“书本中的法”同“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的局面。因此,要关注中国实践中“行动的法”,即政法工作机制是什么?如何运转?政法传统如何形成?
最后,侯猛教授认为学者可以通过研究一系列的政法关键词,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许多法学的标识性概念来自于政法工作的经验,然而政法工作经验中有许多概念不为法学研究者所关注,比如协调、过问、督查和巡视等也是需要关注的政法关键词。而现行宪法中,诸如革命、人民、祖国、妇女、劳动、民族团结等语词或概念,如若不从政法角度进行研究,是无法变为所谓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当中的内容,也会让中国的法学知识体系永远依附于西方。
就此层面而言,建立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需要去了解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历史,形成研究自觉。这种自觉并非是一种隔绝,而是如费孝通先生所题的文化自觉,通过“我看人看我“,来塑造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所形成的标识性概念才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国际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政法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法律中的诸多政法关键词也能够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四 提问互动环节
肖滨教授首先对讲座进行点评,并以两个“赞成的判断”肯定了侯猛教授的研究。他指出,除了《人民警察法》外找不到政法的概念,说明政法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的判断,他是赞成的;从中国法学尤其是从社会科学视角进入,从理解中国政治法律运行的体系而言,政法是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概念,他是赞成的。不过,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
肖滨教授理解侯猛教授所强调的走向法治进程的观点,他也赞同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人权概念的出现作出“从政法走向法治”的判断没有问题。不过,就现行法律运行体系而言,现实状态仍然是政法逻辑同法治逻辑并存的结构。对于如何理解政法是一个标识性概念,他认为要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政体制中来把握,这恰恰是政治学研究的优势。肖滨教授认为,认识政法的运作或者法律体系时要注意政法逻辑和法治逻辑的交织,当下我们正在从政法逻辑逐步转向法治逻辑,还需要从政治学或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角度方能阐释清楚。
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肯定了肖滨教授的看法,他认为政法概念的确需要增加政治的逻辑来理解,但政法实际上是讲政治,从功能意义理解权力而言,政治学同法学对权力的理解会有区别。不过政治学和法学的理解都是一种社会科学倾向的,本质而言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对于要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标识性概念而言,概念本质性的规定不可缺少。
最近,法政治学似乎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存在,例如上周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首届新时代法政治学论坛,但法政治学其实有争论。20世纪奥地利著名的法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甚至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纳入到法律框架下。对此,政治学学者则认为法不能穷尽政治社会,法不能将政治吞并。换言之,政治活动的本质一定是存在的,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的治理强调的是法治,在法治中又如何将政治的逻辑和法律逻辑协调起来?
在2000年左右,不少法学家提议将政法大学改为法政大学,因为民国时期便有许多法政学堂,但是随后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使这一争论复杂化。《宪法学说》讲述政治的法律概念,强调法律运作过程中有一种政治决断,也就是政治的本质不可能被法治国的概念穷尽的,而我们现在的法治思维基本上只有法治国的思维。《宪法学说》有两部分内容,前半部分讲述政治法的概念,后半部分讲述法治国的法概念,施密特没有指出何者更重要,但显然如果将法治国概念提到唯一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政治存在的忽略。黄涛副教授其后指出,如果说政法的概念是向法治概念的转变,试图用法的思维去涵盖政治社会,政治的思维和法律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起来去处理中国的现象。他还认为,只从现象描述的角度恐怕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政法概念在中国的确有其传统,将其提升为一个概念还需要对其作内在逻辑的说明。
吴重庆教授提及政法与法律兼容性的问题,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又该如何回应普适性的法律话语?
对于肖滨教授的提问,侯猛教授指出,政法的实际运行本身就和制度逻辑存在背离。例如,宪法一百四十条规定的是法院(法)、检察院(检)、公安(公)的顺序,但实践中的顺序是公、检、法,因此,就有行动中的政法和文本中的政法的差异。行动上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文本上的逻辑,这种冲突未来还可能一直存在。但就趋势而言,政法逻辑要追求与法治逻辑的内在统一。
此外,侯猛教授认为,政法概念的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并不冲突,可以相互补充。两者都很重要,从党政体制的角度研究更像是外部视角的研究,或者说是从宏观到中观、中观到微观的研究,法学研究则是从微观到中观、中观到宏观的研究。法学做政法研究,注重对公检法的三者或两者的关系,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各个政法单位与党委政法委的关系进行展开经验研究。这种微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具体制度、具体案例的研究,是内部视角的研究。内部视角研究似乎法学比较好做。所以,一个是从外向内的研究,一个是从内向外的研究,这两方面的政法研究都是必要的。政治学与法学一起研究,会使得政法研究会更有活力。学术研究多了,学术话语就会越多出现,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与政法有关的标志性概念、政法关键词就会越来越多。
对于黄涛副教授的提问,侯猛教授认为,在分析意义上,政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这两套思维似乎很难兼容,甚至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讲究的是法律的本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强调法的阶级性,那么法治本身就是政治的法治。
在回答吴重庆教授的问题上,侯猛教授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一直关注并解放被压迫的阶级,聚焦于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这三部法律分别涉及农民、工人和妇女。这是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今天,从政法到法治并不是一个彻底转向。从政法到法治并非是断裂的历史过程,是在不断追求发展,与国际对话的过程。我们的政法工作更加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也是在分享全世界共有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增量的过程。
最后,吴重庆教授向侯猛教授“隔空”赠送讲座纪念海报,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