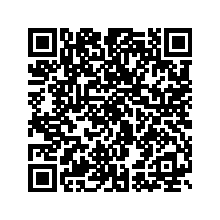2023年5月18日下午15:00,“分析现象学”系列讲座(5):“明证性与可错性”于中山大学锡昌堂515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主讲人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忠伟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郑辟瑞教授。讲座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多名师生共同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李忠伟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问题背景。古人追求确定性,认为存在确定无疑的知识;今人害怕不可错性,认为没有命题是永远正确的。这种当代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对胡塞尔的知识与明证(Evidenz)理论的解读。根据经典解释,现象学的本质知识需要认知地位超凡的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由此获得确定性知识。然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斯特罗克(Ströker)、图根哈特(Tugendhat)、贝格霍费尔(Berghofer)等人反对“存在决然明证”的这种经典解读,并提出可错论解读。李忠伟教授指出,这种日趋主流的可错论解释路径大体是错误的,而经典解读大体是正确的。胡塞尔本人确实持有某种关于现象学的可错论,但这种可错的源头不在于决然明证的可错性,而在于其方法的可错性。李忠伟教授认为,这种关于决然和充分明证的现实性和不可错性的观点与关于现象学及其方法的可错论是完全兼容的。
对于什么是胡塞尔明证理论的经典图景这个问题,李忠伟教授结合胡塞尔的具体文本与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说明与论证。首先,详细介绍了胡塞尔“明证”概念的意义、性质和功能。明证作为意向性经验,在其中意向对象自身显现或给予出来,并被直观到。其次,尽管胡塞尔在早期文本中认为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在外延上相同,但是对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仍然有不同刻画和不同的典型事例:充分明证的典型是对于自我意识生活的内在知觉;决然明证的典型则是关于本质和本质规则的本质直观。胡塞尔明证理论的经典图景就是指存在确定的、不可错的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在所有原则的原则上犯错。李忠伟教授指出,或许有人质疑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的确定性,但是胡塞尔都对这些质疑有所回应:(1)关于充分明证,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充分的感知,而且只有在我们纯粹理解它们的范围内,而不是在统觉上超越它们;(2)关于决然明证可错论的谬误,其原因在于混淆了明证与明证感觉。
当今学者对笛卡尔式的基础主义和明证之不可错论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胡塞尔明证理论的经典解读。根据斯特罗克(Ströker)、图根哈特(Tugendhat)、贝格霍费尔(Berghofer)等人的可错论解读,胡塞尔在中后期认为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没有现实性,所有明证都是可错的。李忠伟教授指出,Berghofer诸人的可错论解读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支撑、关系为表里源流的论题。(1)论题1:关于明证本性的内在现象性论题:明证与意向性相联系,因为原初给予性的现象特征[完全]揭示了明证的本性。(2)论题2:明证可错论题:明证皆可错,即便决然明证也是可错的。李忠伟教授认为Berghofer的思想论证存在漏洞:在论题1中,Berghofer所谓决然明证的现象特征是指“决然性的现象性体验”。由此,Berghofer提供的文本证据和心灵复制人的思想实验,仅仅证实了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可错的,但不能证明本质明证自身的可错性。因此,李忠伟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Berghofer等人的理论分析和文本证据,真的足以支持可错论解读吗?
李忠伟教授认为,胡塞尔对早期明证理论进行了精修而非拒斥。胡塞尔对早期明证理论的精修体现在重新考察了明证的概念及其范围,在概念和外延上明确区分了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而且胡塞尔在中后期继续坚持充分明证和决然明证的实在性。李忠伟教授指出,Berghofer等人的可错论论题的核心症结在于“现象特征”。根据胡塞尔现象学的“现象特性”理论可知:第一,“现象特性”至少应该包括:1) 意向活动的质性;2)意向质料;3)意向对象;4)明证的经验模态。第二,要区别对待感性明证和决然明证:1)感性明证,即所感知事态的成立确实并不参与构成感知明证;2)决然明证,即拥有关于q的决然明证蕴含q必然为真。李忠伟教授认为,Berghofer等人所列举的文本证据仅仅表明感知性明证是可错的,并未提及决然明证;心灵复制人的思想实验可以在感知性经验方面拥有相同的现象学特征,但不能在决然明证方面使得所有现象特征相同。由此,李忠伟教授认为,与可错性联系,有三种可能解读方式:1)所有决然明证都是可错的;2)有些决然明证是可错的;3)表面上是决然明证的伪决然明证是可错的。Berghofer等可错论者可能支持1)或2)。但李忠伟教授认为,胡塞尔真正支持的是3),这无论从文义还是理论上都更有道理。最后,李忠伟教授通过援引莫汉蒂(Mohanty)和霍普(Hopp)的论点来为现象学方法可错性与决然明证的不可错性作辩护:现象学学科与方法是可错的,但这并不表明决然明证是不可能的。
李忠伟教授认为,决然明证的不可错性和现象学的可错性实际上是兼容的。现象学的方法分为:M1(设置范型)、M2(想象生成)、M3(相似模式提取)和M4(本质抽象),而本质直观在最后阶段出现。正如霍普区分了方法可错性与主体可错性,将现象学的错误归咎于主体可错。因为主体可错、感知可错,所以在进行想象变更时有可能会犯错,因此现象学可错。但是,即使想象变更的方法本身和执行过程是可错的,也不代表方法不可靠。只要现象学方法是可靠的,可错的主体在很多时候也能发现不可错的决然明证。最后,李忠伟教授总结道,有限的主体和严肃的科学都具有可错性的特征,可错性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认知以及有可能去纠错,也意味着现象学或者哲学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改进认知的科学性事业。
在讲座的最后,郑辟瑞教授对李忠伟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并表示本次讲座是充分体现分析现象学特征的一次讲座:结合胡塞尔研究和分析哲学的论题来重新解释胡塞尔的文本。在问答交流环节,现场与线上的多名师生展开了提问:(1)如果借用现象特征来解释意向活动,那么两个不同的信念在现象上有什么区别?(2)尽管现象学方法可错而决然明证不可错,但如何解释“某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决然明证”这种情况?(3)还有多名师生围绕着“胡塞尔的明证性”、“主体可错性”以及“数学知识”等主题进行提问。李忠伟教授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精彩的回应和解释。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