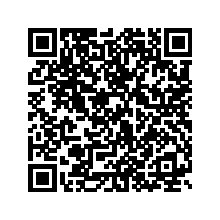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第六讲纪要|张清江:宋代理学家“家祀中霤”的实践及其信仰意涵
2023年3月31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2022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在锡昌堂103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南宋理学家“家祀中霤”的实践及其信仰意涵》,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副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主持。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副教授

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
讲座伊始,张清江老师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了解释。“中霤”是儒家礼典确定的家居“五祀”之一,主要指房屋所在地的土地神。此次讲座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南宋理学家群体,聚焦于他们在自家居所之内祭祀“中霤”的实践活动,以此探究他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祭祀,以及这种行为会对他们有什么价值意义的影响。张老师指出,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考察儒者具体的礼仪实践来深入理解儒家的精神传统,以及这种精神传统在具体生活中产生的意义与影响方式,借此,既可以拓展学界对理学家的既定印象,又试图省思儒家祭礼的神圣向度及其作用方式,并深化宗教学视域下对儒家研究的实质性展开。
一、实践:理学家与“中霤之祭”
张老师首先从文本材料出发,呈现了理学家生活中“家祀中霤”的具体实践。《朱子语类》所载朱熹晚年的生活状态中,有每日“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的说法,表明朱熹有奉祀居处土地神的礼仪实践,而按朱熹的理解,当时流行的家居“土地”祭祀,即是“五祀”中的“中霤”。此外,朱熹文集中留下多篇祭祀土地神的祝文,也可以确切表明,祭祀土地神是朱熹在自家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除朱熹外,对于南宋理学家私家奉祭“中霤”的实践,还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比如,陆九韶为陆氏家族生活订立的《陆氏家制》中,规定每年收成要留“一分为祭祀之用”,明言“祭祀谓先祖中霤社稷之神”;象山弟子、慈湖先生杨简留有两篇祭祀“中霤”的祭文,其中提到“某今家于此依神而居……某敢不敬修其在人,以敬事神”等说法,可以确定是对自家屋室居处的土地神祭祀;朱门高弟陈淳延续朱熹的做法,在家“特立中霤一祠,以朝夕致其奉事祈报之诚”;真德秀在自建“梦笔书堂”时有专门祭告“土地”的祝文,表明他接受并实践着宅舍动工修整时需要“解谢土神”的普遍观念。
张老师指出,这些材料绝非理学家奉祀“中霤”实践的全部,因为家居场所内的祭祀行为并不像为官时的公共仪式一样具有开放性,也很少会留下相关文字记录,但它们的存在很可以证明,祭祀“中霤”的行为实践,普遍存在于理学家群体的生活和信仰之中,并非只是朱熹那里的孤立个案。同时,正因为家居祭祀不同于为官等特定身份下的公共仪式,更能够彰显理学家基于自身信仰而展开的行动选择,凸显其自主性和创造力。因而,这类实践蕴含着理学家的特定信仰经验,同时反映着“神圣”在儒者生活中的作用方式,通过将这类行为放置于宋代社会的整体脉络中,可以很好地揭示儒学传统对于精神秩序的建构,及其如何在儒者的生活中发挥影响。而要真正理解这类祭祀实践对理学家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经验,单单指出其存在的普遍性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呈现理学家在何种信念下做出这一“有意义的”意向行为。
二、观念:“中霤”意涵及其推进
张老师继而分析了“中霤”信仰的传统及其历史演进。《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的说法,提示了“中霤”与社神崇拜的内在关联性,“中霤”就是社神在家庭空间内的表达符号,包含着在宅室特定位置祭祀特定神灵的双重维度,但这两个维度在历史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状况,并交织演进成为理学家们需要面对的思想和礼俗背景。
“中霤”一词的原初含义,跟屋宅居所的特定位置有关。按照孔颖达等学者的疏解,它是古代复穴建筑屋顶中央取光的天窗或天井,那里也会成为雨水汇集的地方,因此被称为“中霤”。“中霤”成为家中祭祀“圣地”,承担作为与神灵沟通的空间通道,与其“居中”“通明”等特性密切相关,因为地中可以沟通神圣,并经由向宇宙的开放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不过,随着房屋形制的改变,尤其是宫室建筑的出现,原本在复穴中位置确定的“中霤”,情形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地理空间的“中”与“取明”(窗牖)、“承雨”(檐霤)等与宇宙天地之气相联的位置发生了分离,由此,关于“中霤”祭祀的位置,产生了“堂室中央”(或中堂)、牗下和屋外等不同说法。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基本接受孔颖达的看法,认为“今之中霤,但当于室中祭之”(《朱子语类》卷九十)、“土主中央而神在室”(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可见,在理学家看来,居“中”是中霤最重要的神圣属性,并接受其因“位中央”而为“五祀之首”的看法。
至于作为祭祀对象的“中霤”,跟“社”的土地信仰密切关联,这点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但家宅土地祭祀的普遍化,则是包含着社会发展和礼思想变迁的共同结果。在《礼记》等文本中,“中霤”作为“五祀”之一,与门、行、户、灶等神灵一起,共同构成与屋室居住者关联最为密切的神灵。不过,在具体的礼制规定中,《祭法》和《曲礼》所述存在差异,焦点在于士大夫阶层能否行祭“五祀”,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经学论争,但可以确定的是,《礼记》“家主中霤”主要指的是卿大夫以上阶层的祭祀,而不包含士庶。但到了宋代,“土神在民亦可祭”的观念已经被士人和理学家普遍接受,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作为“室宅之神”的土地,与家庭生活的密切关联性,如陈淳所说,“土位中央,神实为尊而居地之主,在有家所不容废”。
当然,理学家接受并在事实上推动着以“中霤”为核心的“五祀”实践普遍化,并不意味着理学家完全接受当时民间社会的信仰方式。从理解理学家精神世界的角度,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理学家如何理解对中霤“神”的奉祭?
三、经验:中霤之“神”及其体验
张老师指出,理学家对 “中霤”神的祭祀实践,首先以相信中霤之“神”的真实存在作为前提。陈淳提到“五祀”说“五者之神无不具,亦以人之所居,虽有小大之差,而五者之事则无不同也”,《朱子语类》中朱熹说“古圣人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并明确反对学生“只是当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的说法,都清楚表达了对家居神灵实在性的肯定。在理学家的观念中,圣人制礼作乐,植根于“天理之自然”的神圣根基,礼与天地之道的运作相符应,是圣人基于“观象”体味“天地之德”,进而“循天之道”确立的行为法度,是“天秩”“天叙”的人间展现。因而,不能单纯从人的内心情感这一单向维度去理解儒家祭祀,儒家祭祀礼仪的价值系统,及其包含的对儒者身心形塑和生命转化作用的教化意涵,始终以对天道秩序整体中鬼神的真实性和神圣性为信仰前提。不同于民间信仰的人格化方式,并不意味着对“神圣”本身的否定。
理学家杨简在其“祭中霤文”中对“神”的意涵有完整表述,“阴阳不测之谓神,妙万物之谓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谓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诚,中霤以是灵”(杨简《慈湖遗书》卷十八)。张老师认为,这三个表达从不同维度共同构成了儒家认为“神”在宇宙中运作的基本的存在方式:“阴阳不测之谓神”表达着“天”(理)在“生物”意义上一种来自本体论的神妙性与不可测度性;“妙万物”体现着天地造化遍在于万物的具体落实及其效应;“洋洋如在”则是神显现于祭祀空间以回应人的诚敬感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奠基于前两者所激发的“人道”回应。天地可以生成万物,人能以“诚”立于“三才”之列,都源自“神”的存在和妙用,“神”遍在于万物生化之中,也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这也是朱熹说“盈天地之间皆神”的意涵。就此而言,神是天道秩序在万物生化过程中内在、终极的神性力量,它作为“天德”(张载语)支撑着整个宇宙的运作。
由此去看理学家对中霤“神”的象征性及其秩序体验。张老师指出,“土”最重要的原型象征意义是“创生”,是生命力的源源不断及其对死亡的超越和更新。中霤虽然只是负责家居所在地的土神,但就其“神”本身而言,则通达天地万物,它是宇宙神圣性在家居空间的象征符号。在理学家看来,“中霤”之所以成为需要祭祀的对象,源自其“神”带来的灵妙效果,这效果在根本上属于天道秩序的组成部分。因而,理学家对中霤之“神”的祭祀(跟其他祭祀一样),首先意味着人体认并参与到天地所构建的宇宙秩序之中,是对天道和神圣秩序的生存论回应。
理学家的“中霤之祭”,首先建立在对中霤之“神”的真诚信仰之上,建立在中霤作为神圣宇宙的象征显现(“圣显”)这一基础上。这一“神”的概念不同于原初人格化的“天神信仰”,但仍保留着其作为天道秩序生化流行背后神圣力量的超越理解和体验。因而,理学家始终坚持,自己生活的家庭,是一个与宇宙秩序相通、向宇宙开放并充满神圣性的空间,其作为安居之所,以人对天地的依赖和关联为基础,充满着宇宙秩序的神圣象征。对理学家来说,祭祀“中霤”正是这种信仰的实践表达,并透过这一实践使家居空间与天地造化相联系,使居所得以“圣化”,也使自身生活与大化流行的宇宙秩序相协调和感应,因此,它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与宇宙生命本源接应感通的超越性经验。
四、结语
张老师最后指出,“五祀”神灵是宇宙力量在家居空间的“显现”和象征物,是居所与宇宙相互关联的通道,借由对它们的定期祭祀,“房屋”得以与宇宙中心重新连接,使居所空间中的人、事、物,均指向超越人类生活自身的终极神性实在,并由此使得居所空间成为“有意义”的世界。理学家正是在相信中霤之“神”真实存在且为“五祀之首”的基础上展开其奉祀实践的,这一行为本身表达着他们对“神圣”的追寻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落实。
由这一实践可见,理学家其实跟很多传统民众一样,相信自己生活于一个充满“神”的宇宙之中,认为天地间所有事物都有显示自己神圣力量的形式。不同之处在于,理学家的“神”作为宇宙生化流行的灵妙与力量,要求的是人对天道召唤和神圣宇宙秩序的回应性参与,而非将其作为解决自身现实困境的人格存在。这种差异来自两者对神圣如何显现于世俗世界的理解不同,但并非对是否承认“神圣”本身的不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家对民间信仰作为“淫祀”的批判,不是宗教与反宗教、信仰与反信仰的差别,而是不同信仰形式的区分。
五、评议与问答环节
讲座结束后,吴重庆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吴老师认为,张老师认为对儒家祭祀的研究应当关注对“神圣”向度的信仰,的确拓展了仅从社会功能视角来理解的研究方式。进而,吴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儒家最关注的祖先崇拜问题,南宋理学家如何处理?第二,为何南宋理学家能够接受庶人祭祀中霤?张老师回应说,祖先崇拜的问题,朱熹主要从理气论的角度给予解释。朱熹一方面强调人死后气一定散尽,另一方面又强调祭祀空间中有真实的祖先之气发生感通,其论证方式是,祭祀者以内心诚敬去祭祀祖先,可以产生“根于理而日生”的新生之气,新生之气既是真实的祖先之气,又非祖先的生前之气。其次,南宋理学家对于士庶人家祭祀中霤的态度,与社会的变迁有关,并与理学家对祭礼的理解相关。中霤与家庭每个人的生活紧密关联,符合理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与祭祀对象的“相关性”要求,因而从“礼以义起”的角度可以接受。
对于现场同学提出的“不同家庭祭祀的中霤是否是同一个神灵”和有关“淫祀”等问题,张老师也一一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