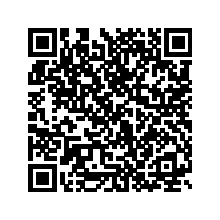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第五讲纪要|杨小刚:意向性概念的诞生——阿奎那对形质论心灵哲学的突破
2023年3月24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2022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五讲在锡昌堂103室举行。讲座主题为《意向性概念的诞生——阿奎那对形质论心灵哲学的突破》,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杨小刚副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田书峰副教授主持。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杨小刚副教授
一、意识在自然中的位置
讲座伊始,杨小刚老师通过引用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中的一段话预示了本次讲座的一个终极联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走在各种学科之前的物理学现在正对精神越来越倾向于肯定;而生命科学则仍旧走在上一个世纪的物理学的路上,现在正试图完全取消精神。心理学家哈罗德·莫洛维茨对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如此转换对精神的看法提出了如下的评论:“实际情况是,生物学家们以前认为人的精神在自然界的分类等级之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现在则义无反顾地走向赤裸裸的唯物论,而19世纪的物理学就是以唯物论为其特色的。与此同时,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实验证据的物理学家们则脱离严格机械的种种宇宙模型,转而把精神看作是一切物理事件中扮演着一个与事件不可分离的角色。这两个学科就像是坐在两列逆向飞驰的火车上的乘客,彼此都没注意到对面开过来的火车上正在发生什么事。”
在当代哲学研究的推进和发展中,尤其是分析哲学当中,物理主义可以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当然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物理主义,但无论哪种物理主义都试图将心灵、意识这样一些我们视为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概念用那些自然的概念来进行解释。而令人诧异的是,许多物理学家对于心灵、意识越来越有着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杨老师试图通过分析意向性概念在形质论心灵哲学框架中的产生过程,为心灵或者说意识在自然中的位置,寻找一些不同于现在比较占主流的物理主义的解释。
二、关于感知的物质论与精神论
杨老师首先介绍了布伦塔诺和索拉布吉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感觉”定义的不同理解。布伦塔诺在《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中说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对象的意向性(或心灵的)非存在,是每一种心理现象的独有特征,我们会称其为指向内容的关联,对象指向,或者内在的对象性,尽管这些表达并非没有歧义。”也就是说,我们心灵中的各种各样的表象,无论是感性的、想象的、认知的、欲求的等等,所有这些心灵内容都是关乎某个对象的,都指向某个对象,都具有一种指向性。这就是“意向性”。布伦塔诺还特别强调这是“每一种心理现象的独有特征”,以此与物理现象、自然现象相区分。布伦塔诺认为在经院哲学那里就已经发展出了“意向性”概念,不过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暂时只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对象相关性、对象指向性在阿奎那那里虽然可以有所引申、有所联系,但尚未完全发展出来,阿奎那的思想更多的体现了布伦塔诺所说的另一重含义,即“心理的内驻(psychische Einwohnung)”。布伦塔诺提到,所感作为被感知的在感知者那里,感官获取所感但并不获取质料,所思在思维的理智中。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的最后一章中对感觉作出的一个一般的定义:“感觉(或感官,aísthesis)接受可感物的形式,但无质料。”(DA II 12,424a18)就是这一定义使得布伦塔诺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可以通向“意向性”概念的痕迹,或者说是一个铺垫。布伦塔诺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可感形式是内在于心灵的。
索拉布吉(Sorabji)则重新审视了这一定义,提出了和布伦塔诺不同的看法。索拉布吉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并非感觉,而是感官,是“感官接受可感形式,但无质料”。感官与感觉自然是有区别的。感官是我们身体的感知器官。感觉则是一种能力,在中文里,说到感觉的“觉”,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觉”是一种内心的呈现。感官具有感觉能力,感觉依赖于感官。索拉布吉就是要强调这样的区分,他认为“接受可感形式而不接受质料”的是感官而不是感觉。他给出一个例证——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眼球会变成对象的颜色。即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眼球里面都会有外在对象的“投影”,虽然微小,但是纤毫毕现,各种颜色都呈现在其中。基于这样一种自然的经验观察,就可以说眼球变成了对象的颜色,如果我们看一片红色的东西,眼球上就会有红色的“投影”。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提供的一个例证(DA III 2,425b22 f.),索拉布吉将之作为典型,据此认为接受可感形式的是感官本身,感官发生了一种形式上的接受,具有了这种形式所指称或者说所确定的一种属性。正因为这样一种形式上的接受可以在经验上进行观察,索拉布吉借此给出了一种生理学的解释。
索拉布吉基于这样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学说尤其是感知学说,做了一般的生理学的解释。其相关的文本依据还有很多,比如:“虽然植物拥有部分的灵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被接触到的对象所影响,它们既可受热,也可变冷,但是植物却不能感觉。其原因在于它们不具有中道,没有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本原,仅只承受质料的作用。”(DA II 12,424b1 f.)杨老师由此点出了生理学解释的两个面向:首先是“Affected without matter”:感官接受可感形式是一种生理变化,例如看红色眼球会变红,但这种变化并不会获取可感对象的质料,例如在蜡上盖了金印的形状,而蜡并不摄取金印的质料;其次是“Affected with matter”:植物会被染色,是通过获取外在有色物的质料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一种生理-物理变化,但这并非感知。
介绍完上面的两种理解之后,杨老师提及物质论与精神论解释在文本解读上的一个关键分歧。在面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的“τί οὖν ἐστι τὸ ὀσμᾶσθαι παρὰ τὸ πάσχειν τι?ἢ τὸ μὲν ὀσμᾶσθαι καὶ αἰσθάνεσθαι, ὁ δ' ἀὴρ παθὼν ταχέως αἰσθητὸς γίνεται?”(What, then, is smelling beyond being affected by something? Or is smelling also perceiving, whereas the air which is affected quickly becomes something perceptible?)(DA II 12,424b16-17)时,物质论将其解释为:除了受外物作用,闻也是感知;而精神论将其解释为:相对于受外物作用,闻即是感知。物质论的解释认为感知包括受到外部的作用,也包括闻这样一种活动。而在精神论看来,除了“闻即是感知”之外,还要把beyond being affected by something翻译为“相对于受外物作用”,也就是说受外物作用不被纳入到他们所认为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感知的理解当中。这主要是强调一点——感知是仅仅发生在意识层面、心灵层面、精神层面的。
物质论解释在整个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学说里其实是和其他的一些论述更为融贯,它十分符合亚里士多德对于心灵的形质论的解释。而心灵形质论又可以和当代心灵哲学里的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功能主义顺利接洽。物质论解释认为,感知是基于感官的生理变化而实现的心灵活动,生理变化是质料,心灵感受是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形质论则是心灵是具有生命的自然肉体的形式,人的身体是质料,心灵是形式,心灵赋予了身体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形质论本身就支持了功能主义的理解——心灵是身体潜在的具有生命活动的实现,就像视觉是眼睛的实现、工具的功能是工具的实现。
但物质论其实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
1. 可感形式被感知和感官接受可感形式是同一个实现活动,但如何理解感官的某种生理变化是可感对象的一种实现?镜子照出物体是否是物体的一种实现?
2. 如果感知到F即意味着感官变得F,例如看到红色眼球就变成了红色,那么看到番茄是否意味着眼球会变成番茄?
3. 如果“接受可感形式,但无质料”指的是不获取可感对象的质料,则必须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五种感知均不涉及质料的摄取,但嗅觉和味觉可能构成反例,且必须认定对无感官之物的作用都涉及质料的转移,但发声引起震动会构成反例。
同时,精神论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精神论认为,“接受可感形式,但无质料”指的就是对可感形式的意识,是纯粹心灵中的呈现,没有任何所谓的生理变化。所谓心灵的质料是身体的状态,而不是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接受可感形式是在心理层面发生的一个变化,而不是一个生理的变化。精神论解释否认身体变化,因此也就反对功能主义的解释。
三、阿奎那的突破
物质论和精神论解释争议的文本,恰恰是阿奎那据以提出意向性概念的基础。所以在梳理了两种解释之后,杨老师介绍了阿奎那对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理解:
For the form has a different manner of being in the sense and in the sense object: for in the sense object it has natural being, whereas in the sense it has intentional or spiritual being. (In DA II 24,45-59)
针对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提出的那个感觉的一般的定义,阿奎那认为,形式有着不同方式的存在,在可感对象那里,它是“自然的存在”;而在感觉中,它是“意向性存在”(esse intentionale)或者叫“精神的存在”。在阿奎那看来,所有变化的主动者(agens)都是依靠形式发生作用,被动者(patiens)均是接受形式而无质料,如火加热气,气并不获取火的质料,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的定义初看并无特别之处。不过,被动者接受的形式与主动者的形式在存在的模态(modus essendi)上有相同和不同,若被动者与主动者的质料有同样的势态(dispositio)则相同,有不同的势态则不同。如果被动者的质料与主动者的有相同势态,则会在质料和形式上都变得像主动者,是为“接受可感形式,且有质料”;如果势态不同,则仅在形式上变得相似,是为“接受可感形式,但无质料”,感觉即如此。可以说,阿奎那恰恰是为了进一步辩护和解释Affected without matter和Affected with matter的差别,提出了意向性存在一词。
我们发现,阿奎那的理解接近当今精神论的解释,但是也不并不完全支持精神论,因为他另一方面提出的新理论是质料有不同的势态。眼睛看颜色的例子在他这里就变成了:眼睛看颜色时是仿佛(tanquam)眼球有了颜色,颜色在可感物和感觉中有不同的存在,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精神的。
我们回到“意向性”这一概念上来,其实在阿奎那这里我们还看不到“意向性”非常充分完整的理论发展。有学者统计过,“意向性”在阿奎那这里总共出现过十二次,这十二次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否认时人认为的光具有意向性或者精神的存在;
第二种,解释天使的知识具有意向性存在;
第三种,对象在感觉和理智中的形式具有意向性存在。
杨老师指出,阿奎那的这些用法尚未呈现出心理现象独有的对象相关性这一层含义,但是恰恰因为在他这里展现出意向性从形质论心灵学说中产生的清晰脉络,我们可以由此把握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心灵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统一图景。
由此,杨老师分析了意向性存在的几种理论功能:
首先,在认为所有变化都通过形式发生作用的前提下,可以解释感知和认识为何是对象更高层次的实现。按照形质论这样一种潜能-现实的学说,所有的自然存在者都有不同层次的实现,而当它最终的被感知和被认识也是这个自然存在者的一种实现时,这种实现按照阿奎那意向性存在这个概念所标明的,它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模态的实现。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它都内在地具有一种在精神上获得实现的潜能,而这样一种心灵层面的实现,是它自身自然存在着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实现。
其次,在认定感知属于偶性变化后,避免感知一个对象即变成一个对象的荒谬结论。
最后,在同一、相似、因果性、形式-质料关系之外,使意向性关系成为必须被探讨的一种可能的原初(primitive)关系。当然这个原初性我们或许可以不承认它,我们可以对意向性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很盛行的物理主义解释,也就是把意向性还原到因果性的一种自然的变化上面去,或者把它还原到其他的比如同一性、相似性上面去。但阿奎那文本中凸显出来的,可能是它恰恰能被还原为其他这些关系,它是一种原初的关系。
最后,杨老师给出了“一个联想、两个困难”,留给所有感兴趣的同学们思考:
一个联想:如果自然物潜在地具有意向性存在,意向性存在是其更高的实现,则可能发展出某种关于自然与精神关系的统一理论。
困难一:如何解释主体意识结构的位置。
困难二:如何解释身体的作用。
四、评议环节&问答环节
讲座结束后,田书峰老师对整个讲座进行了评议。田老师认为杨小刚老师的讲述十分详细,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方面,做了一系列精细的文本考究,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对于物质论解释和精神论解释与意向性的关系问题,杨老师说道,索拉布吉反对布伦塔诺关于亚里士多德文本做的意向性的理解,正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不同解释,他发展出了物质论的解释。索拉布吉不同意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有意向性概念的,当然他也要解释心灵作为形式到底是什么含义,但他不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意向性概念。这是在文本上的最初关联。而意向性概念与物质论和精神论争论在问题内部的联系,关键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感形式究竟是指什么。物质论解释认为,身体的生理变化即可感形式的接受,而这就与布伦塔诺所说的心理的内驻没有任何关系了,基于这一点,意向性也就不存在了。至于亚里士多德其他可能引发“意向性”理论的思想,已经属于关于想象力的讨论,而不是在感知这里。阿奎那则恰恰是在感知层面就使得意向性概念得以“萌芽”。
在与田书峰老师交流后,杨老师也与现场同学进行了热烈讨论。比如,对于可感形式和可感对象的统一性问题,杨老师回答说,我们今天只讲了阿奎那,这种统一性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这么明晰。按照形质论的观点,可感形式和可感对象的关系是通过相似性来解释的,但意向性关系恰恰让这种相似性成为疑问,它一方面不接受柏拉图理念论的智性世界本原说,另一方面却可能让自然世界具有内生的精神化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