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三讲纪要|马天俊:马克思的爱国主义
2023年3月10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2022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三讲在锡昌堂103室举行。讲座主题为《马克思的爱国主义》,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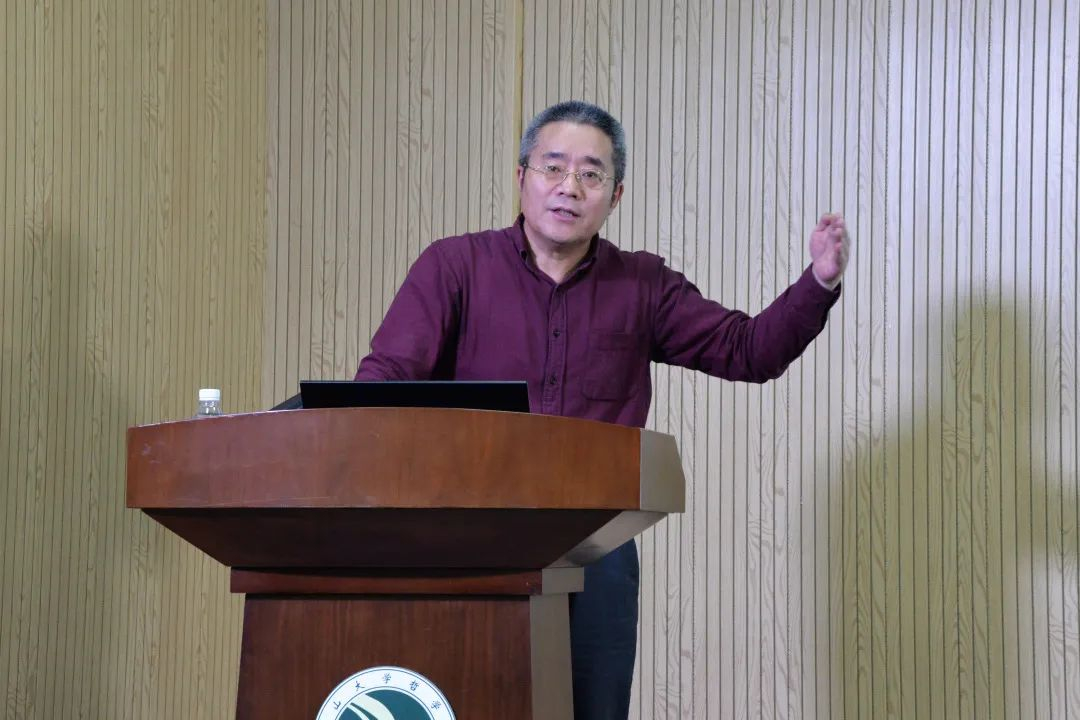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
一、马克思的流亡生涯
讲座伊始,马天俊老师首先对讲座主题“马克思的爱国主义”进行了解释。“爱国主义”既是复杂议题,也是一个大概念,在这里只是就它的某些性质或侧面做一讨论。通常,按马克思的学说,人们不会把马克思和爱国主义放在一起探讨,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显然是世界的、人类的,是国际主义的。其中,“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将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超越,而代以自由人联合体。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并非某种“爱国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现代人,“国”或“国际”这种现代现实又是他人生的处境,爱国主义这种现代情感和现代意识,在他身上也有一种特定的展现。经过这样的限定,“马克思的爱国主义”就构成一个有限但确切的论域,这就是我们这次课的议题。
马老师用一张历史地图直观地展示了马克思的基本生涯。马克思主要生长和活动在莱茵河地区,包括特利尔、波恩、科隆。这个地区是普鲁士最西边的属地,毗邻法国,拿破仑时代曾划归法国或受法国支配,它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风尚更接近经过启蒙和大革命的法国,而不是远在东边的柏林——普鲁士的政治和文化核心。按通常的传记叙述,上中学之前马克思主要在家中随父亲受教育,他父亲是启蒙的拥趸,崇尚伏尔泰和康德。马克思的中学教育也是充满启蒙要素的。这类教养在学识意义上诚然是不够的,不过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和趣味却是奠基性的。大学之后,马克思是在科隆的《莱茵报》的供稿者,很快又成了编者兼作者。《莱茵报》是普鲁士改革年代的言论先锋,它也因此不久就被停办了。从此,马克思的流亡生涯开始。马克思选择的流亡,方向是明确的,就是朝向更自由的地方。马老师指出,流亡(expatriate)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孪生的,在词源上,它们的词根的含义都是父亲。这个含义后来衍生为“故土”、“祖国”。爱国是依恋,流亡是剥离,核心一样,方向相反。“国”古已有之,样式不一,我们在这里要涉及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的现代史上,民族-国家可以说“国”的主要样式。爱国或流亡,也是以这种“国”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向普鲁士官方致信表明放弃普鲁士国籍,也是在这种框架中行动的。
马老师进而通过评论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的文章“时评”来推进议题。这篇文章借助于著名传教士郭士立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他(大概在伦敦)对“社会主义”的评论,既谈了中国,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更重要的是也借此谈了欧洲。这里面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文章说:“(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最后一句宣言式口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化用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则格言“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Unité et 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
按文章,社会主义潮流是郭士立感到在中国在欧洲都避之唯恐不及的,而文章作者却乐见郭士立的这种困窘。值得思考的是,这里用来充实社会主义的那些要素——“自由,平等,博爱”,通常人们的理解是认为它们反映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至于社会主义,应该另有一套。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辩证法,那么,社会主义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反对,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是对资本主义已然开启却因自身历史局限而不能充分实现的人类价值的真正实现。这样想来,反倒是流行意见太肤浅了。其实,现代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也包含在上面的革命格言中,这是我们的讨论要特别重视的。
二、爱国论举隅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三观”(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现代观念史上经历过长久的酝酿和培育,启蒙运动尤其重要,这是众所周知的。马老师援引了17世纪拉布吕耶尔《品格论》的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在专制的国家没有祖国:在那里作为替代的是:利益、光荣、对君主的效劳。”(梁守锵译文)这格言的焦点是祖国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启蒙时代诸多思想家们的紧要关切。例如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故乡,祖国”(Patrie)条有一段文字:“一个糕点铺小伙计,……有一天装出一副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神态。一位邻居便问他:你说你的故乡、你的祖国,是指的什么呀?是你那座烤点心的烤炉吗?是你自出生后就从来没有再见过的那个村子吗?是你那两位破了产弄得你只好去做糕点来谋生的父母住过的街道吗?是你永远也当不上那里警卫官的一名小书记的市政厅吗?是你在那里永远也当不上一名抱蜡侍童而一个愚蠢的人都做了总主教和公爵有两万金路易年俸的那座圣母院大教堂吗?那个糕点铺小伙计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一个国土略微辽阔一点的国家里,却常常有好几百万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乡、什么祖国。”(王燕生译文)又如霍尔巴赫曾在《自然的体系》中说:“做个好公民吧,因为你的祖国对你的安全、快乐和幸福是必需的。要忠实并服从合法的权威,因为于你自己是必需的那个社会需要它来维持。要遵守法律,因为它是公共意志的表现,你个人的意志应该从属于公共意志。要保卫你的国家,因为正是它使得你幸福,维护你的财产以及所有你心爱的东西。当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公共的母亲陷在暴政的铁蹄之下的时候,决不要悲伤,因为那时它对于你已不再是祖国而只是一座监狱。如果你的不公正的祖国拒绝给你幸福,如果它屈从于不公正的权力而遭受折磨,那么,你不声不响地远远离开它吧,千万不要去扰乱它。”(管士滨译文)此类见解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中十分常见。可以说,这样的爱国,注重的首先是“国”与“国民”的良好关系,专制或暴政之下,既谈不上祖国,遑论爱国。“自由,平等,博爱”并不是一般说来泛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是在祖国中自由,在祖国中平等,在祖国中博爱。如果考虑到启蒙的一个现实背景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朕即国家”,这类见解大概就更容易掌握了。实际上,未被现代内容所充实的祖国,其爱国主义往往呈现一种奇特的面貌,就此正用得上同在18世纪的英国名士塞缪尔·约翰逊的愤慨之言“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如果说糕点铺小伙计是可怜的,恶棍就是可恶的了。
在中国现代思想家中,梁启超曾在1899年的文章“爱国论”中阐发一种著名论断:“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在中国观念史传统中大概是一种难得的创见,表明中国已经比较自觉地站在现代的门槛上。从见解到实现,自然还有很远的路。这个时期的梁启超还寄望于光绪皇帝,尽管光绪皇帝也已经自身难保。当然,见解本身也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譬如陈独秀1904年的文章“说国家”中一方面回忆说自己十年前还简直不晓得有国家这回事,只是甲午、庚子才教他明白起来,另一方面,他笔下的“爱国”,大体还处在“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的层次,尚未触及“民权”这样的内部问题。他看到受侵略,感到责任大,不过在他眼中,英、法、德、俄一律列入“列强”,这几个国家这个时期差异巨大的内部状况显然还没有得到注意。就陈独秀来说,他再进一步,大概要到1917年看到俄国二月革命的时候,那时他十分敏锐而且及时地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指出欧战中展现的现代大势乃是“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不难看到,所谓德先生,实在是有时代针对性的。数月之后,十月革命发生,敏锐的陈独秀却似乎失去了敏锐性,沉默了一个不短的时间,不过这涉及另外的复杂议题,这里不展开了。
三、《资本论》第一卷与马克思的爱国主义
有了上面关于爱国主义的观念史勾勒和准备,马老师让大家再次把目光转回到马克思的流亡生涯。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告竣,马克思带着书稿到汉堡与出版商迈斯纳商量安排印刷,期间他又应邀到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家小住。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马克思在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尔德律师到我这儿来(不要告诉别人)。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俾斯麦的意向看来是希望马克思与普鲁士国家达成某种合作。应该说,这并不是全然无理的尝试。事实上,广义的社会主义潮流中,有些潮流是愿意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例如拉萨尔的派别,这样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的,要加以强调的话,应该称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是社会运动,不是国家主导的运动,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不是国家解放无产阶级,相反,国家正是在现代阶级斗争的社会运动中要消亡的。国家常在,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依靠国家进行,一旦依赖国家,就又陷入到旧的历史形式中了。况且,国际工人协会也正在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作为其中灵魂人物的马克思在政治上也是不便与俾斯麦搞什么合作的,所以马克思跟恩格斯强调这来访本身都不要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意味着马克思的爱国主义必定不是通常所说的那一种。
马老师接着引入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并且通过目录为大家展示了该卷的内容编排结构。马老师认为,马克思对祖国的关切主要显现在这一卷。该卷正文共有6章,篇幅分布极不均称。按第一章那样的逻辑推演,全书并不需要庞大的篇幅,而那些篇幅明显庞大的章节,满是英国的社会调查材料和议会辩论材料。从理论逻辑来说,适当的材料佐证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这样大量的材料。《资本论》学说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展现出来的有先验结构性的逻辑。那么,马克思这样做有什么考虑呢?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中大篇幅的实证材料有单纯理论逻辑之外的用处。这里且细读一下马克思写的“序言”: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中央编译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有一番夫子自道,解释了我们前面的设问。关于英国工农业工人境况,关于社会统计,关于工厂法,叙述起来的确要用很大篇幅。而之所以这样做,逻辑的必需是次要的,实践的关切是主要的。这种关切,指向马克思的祖国,指向德国人,提示德国人在客观规律之下可能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马克思甚至生动地指出了学习的好处和不学习的坏处。在这个意义上,这位流亡者,并没有忘怀祖国,他以自己的学说向祖国建言,既提示官方,也提示民众。宗旨何在呢?不是为了富国强兵——那是普鲁士的老本行,而是为了人道,为了减轻痛苦。这是启蒙精神中爱国主义的继续发挥。
四、评议环节
讲座结束后,户晓坤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户老师认为,马老师的语言幽默生动,对于各种史料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将马克思与爱国主义两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研究主题建立在马克思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之中,在流亡与爱国的纠缠与张力之中,展现了马克思对于我与祖国、专制与自由、现代国家与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爱国主义之于马克思,是一种责任和眼光,而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原初感情。马老师为我们做哲学提供了以具体承载宏大的独特方法论,尤其是如何直面社会历史的复杂性,避免陷入抽象空洞的词句之中。
五、问答环节
现场同学结合当下社会现象进行了提问,马老师一一做了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共和主义的概念是矛盾的,还是联系的?民族和人民的概念指涉的是同一个对象吗?是否要先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然后才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呢?马老师回应说,民族、民主、国家、爱国等概念是经验性很强的概念,定义和还原都不容易,因此同一或矛盾也就不容易讲。这些概念经常是交错的,例如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似乎要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似乎是国家的根据,不过,民族本身往往又是被国家所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有多种样式,民族国家和民主在概念上并不冲突,当然也不必然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有长期的流亡经历,梁启超、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是动荡的,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受到环境影响而生发出来的,而我们当下所处的年代是和平年代,那么爱国主义是可教的吗?如果是可教的,被教的爱国主义与马克思、梁启超和陈独秀深切感受的爱国主义有何区别?如果是不可教的,我们能否生发出像他们一样的爱国主义?马老师回应说,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爱国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现代情感。作为后者可以说是不可教的,它需要在环境中耳濡目染和示范;作为前者是可教的,因为前者是可言说的、可论证的。当然,示范和言说也可能会出现分裂的情况,我们可以再想想前面引过的约翰逊的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