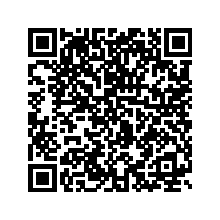伦理学名家论坛第二讲回顾 | 萧阳:孟子的“性之”哲学
2022年6月10日,“伦理学名家论坛”之“中西伦理-政治哲学中的‘心性与秩序’”系列讲座第二讲“孟子的‘性之’哲学”线上开讲。主讲人为萧阳,现任美国肯庸学院哲学教授,华东师大哲学系客座教授。本次讲座主持人与评议人分别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乔见教授与杨海文教授。主持人陈乔见教授首先介绍了萧教授的研究领域是英美当代伦理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等,同时对中国古典哲学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皆有独到的诠释和理解,充满睿智,往往别开生面。

萧阳教授首先从伦理话语在现代“科学自然主义”兴起之后所遭遇的意义危机切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某些极其残暴的人(比如那些殴打妇女小孩的人)时,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不说,“他不是人”,“他这样做,真是没心没肺”, “禽兽不如”,这一类话就没法表达我们真正的立场,但是,从“科学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却成了无意义的胡说,因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当然还是“人”,不是“禽兽”,而且他依然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心脏”与“肺”。尼采认为,古代伦理学关于人应当“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口号,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我们现代人认为大自然本身既没有怜悯也没有正义,它对于人类及其价值是漠不关心的。韦伯也认为现代科学的兴起必然意味着“世界之祛魅”。在西方哲学界最近才开始被重新发现的“新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自然主义”兴起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伦理学的主流立场是,由于大自然没有意义与价值,“伦理自然主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它建立在“自然主义谬误”之上,是通过从“实然”或“事实”不合法地推出“应然”或“价值”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元伦理学的主流一直是主观主义,表达主义,非认知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立场。它们都认为,大自然中没有规范性,因此规范性只可能存在于主观性中。这个演讲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在汉语哲学界对孟子式的伦理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与真实性与大家一起开始探讨。萧教授指出,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古人的“伦理自然主义”中的“自然”概念不同于现代人的“科学自然主义”中的“自然”概念,前者与物类相关,而后者与物类无关。当古人说到“顺应自然”或“顺性而为”时,他们说的不是现代科学所说的“大自然”或“自然界”,而是与类相关的自然,也就是,“人之性”。尼采与现代伦理学家在嘲笑与攻击古人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时候,其实却犯了“概念混淆的谬误”与“偷换概念的谬误”。
在讨论《孟子》中的有关章节之前,萧教授对于我们应当如何读经作了一个简短的讨论。《孟子》中文字本身的语法,文义或字面意思有不确定性,容许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纳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所采纳的策略,那就是,回到孟子所观察研究的原初现象。他们也意识到,在《孟子》中的句子的文义与《孟子》的真意之间存在空缺与裂痕。但是,由于经是载 “道”之物,是圣人观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道”与“理”,然后以文字的方式遗留下来的陈迹。因此,这些理学家通常会通过诉诸于他们自己对这些原初现象之“理”的研究与体会来填补这些空缺与裂痕。这就要求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回到孟子哲学时他所观察与研究的“原初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与孟子一起哲学”,“学孟子者,当学孟子之所学”。
萧阳教授然后从这一哲学诠释视角,对《孟子·告子上》中的三章中所关注的“原初现象”做了分析。此三章分别为(6A1) 孟告“杞柳之辨”章;(6A3) 孟告“生之谓性”章,(6A19) “五谷”章。
关于6A1。萧教授认为,孟告二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对如下这个原初现象有共同的观察与描述:杞柳树上不可能长出杯碗,杯碗只能是由木匠破坏杞柳树的“性”制作出来的。告子的第一句话明确地说,正像“杞柳树”上长不出“杯碗”, “人性”也不可能生长出“仁义”。孟子同意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原初现象,那就是“杞柳树”上长不出“杯碗”。他和告子在这里都认为,万物生长变化,但是万物的生长变化顺应一定的“道”,“理”。不同的物类其生长变化的方式,因类而异。而决定某一特定物类以其特有方式生长变化的就是这一物类的“性”。“杞柳树之性”决定了它们长不出杯碗。
但是,孟子并不接受告子的第一句话本身。他显然意识到了,只要我们不像告子那样将“杞柳树之性”比喻为“人之性”,将“杯碗”比喻为“仁义”,我们依然可以拒绝接受告子的整句话。我们知道,孟子用了很多来自植物生长的现象作为比喻 (“拔苗助长”等等)。也就是说,孟告之间的分歧在于究竟应当用“植物生长”还是“工匠制器”作为比喻来理解“人性”与“仁义”之间的关系。
萧教授然后讨论6A3孟告“生之谓性”章。这里,孟子与告子之争的焦点在于,告子坚持认为,而孟子则坚决否认,“白”与“性”是两个同类的词。当然,仅仅从这两个词本身来看,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除此之外,它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实质区别。孟子在这里的眼光超越了汉语的形式语法,他考察的是这两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法。孟子在反驳告子时,首先得到告子的认同, “白”这个词是与他所形容的物类不相关的:“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出现在“白x”这个词组中的“白”的意义不会因为它后面所连接的名词x的不同而改变。然后,孟子反问道,“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这显然是一个修辞性问句。其实是一句断言。作为断言的修辞问句与一般的用来问问题的真正的问句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不期待回答。这也是为什么6A3就结束在孟子的这句修辞问句上。那么,孟子对他的这一结论,“牛之性”与“人之性”是不一样的,是如何论证的呢?这里我们需要填补文本中的空缺。孟子一个没有明说的前提是,牛与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而这必定是因为决定它们生活方式的“牛之性”与“人之性”不一样。也就是说,孟子的论证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正是我们在6A1中就已经见到的与类相关的“性”这一概念。
这也意味着孟子对告子在6A3中的第一句话“生之谓性”的解读必定是:“某类生物[以其特有的方式]生长的动力源头是它的性”。这一解读与孟子在其他地方对“性”的用法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用江河的源头作为比喻来谈论“人之性”;在谈论圣人的行动时用“性之”来描写其行动,这里的“性”是动词,是圣人的行动的动力源头。当然这与告子本人在说他的“生之谓性”这句话时的自我理解是不同的。告子显然将它理解为“任何生物在出生时所具有的性质是‘性’”,或者“任何生物生长的动力源头是‘性’”。这与告子的另一句话“食色性也”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对食色的欲望是任何生物在出生时就具有的,并且是它们的生长的动力源头。告子的性一个与类无关的性的概念。
萧阳教授认为,孟子的“与类无关的词”和“与类相关的词”之分预示了英国哲学家彼得·吉奇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吉奇的文章激发了“新亚里士多德氏自然主义”的复兴。在此文中,吉奇区分了两类形容词:一类是与类无关的形容词,如“白的”;而另一类则是与类相关的形容词,如“好的”。萧阳教授认为,孟子之分更广更好,因为孟子之分不限于形容词。
萧教授然后讨论孟子在6A19中关注的另一原初现象:“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 萧教授对此做如下解读: “成熟的五谷是生长成完美的种子。种子如果不长成完美成熟的五谷,就还不如野生杂草。与此类似,仁不过是人性的完美成熟。”假设我们想要研究“狮子”的“狮之性”,我们当然不应当去研究刚刚出生的小狮子,因为它们的狮之性尚未发展成熟。一只尚未成熟的小狮子还不如一只成熟的狼。我们也不应当去研究缺了一只腿的狮子。相反,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把狮之性发展到完美成熟程度的狮子。也就是说,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对性的定义不仅是与类相关的,同时也应当是“完满主义的”,“至善论的”。因此,人之性的具体内容要由圣人有,而小人没有的,仁义礼智等美德来定义。这就是为什么孟子的伦理自然主义既是描述性的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孟子的完满主义的定义与荀子的非完满主义的定义的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孟子的伦理自然主义可以用来回应科学自然主义。的确,孟子是我们今天的“不是人”,“没心没肺”,“禽兽不如”等这类伦理话语的始作俑者,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非人也”这一表达的: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在与类无关的大自然意义上的“自然”,固然没有价值和意义而言;但是,对于与类相关的“自然”, 比如“人之性”,则既具有描述性的具体内容,亦带有规范性的力量。比如,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7B16)。萧阳教授将这句话理解为:“仁,就是人之性; 当我们观察“人”与“仁”的时候,可以发现“道”。这个道就是,仁与完美成熟的人性总是一起出现。这在孟子那里还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最为明显的一个是“堯舜,性之也” (7A30),意谓:“尧舜这些圣人的行动不过是人性表达自己的结果”。这也就引申出萧阳教授所说的又一个原初现象:人性“即真实即活动”,是“性之行动”。它们不同于“假之”行动。后者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动,比如,假借仁义以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萧教授说孟子“性之”哲学是真实的,普世为真的这一点可以被来自俄国与欧美文学中的许多伟大作品所证实,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他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讲座内容结束后,评议人杨海文教授对讲座进行了专业而深入的点评,他认为萧阳教授立足于世界性知识,对孟子人性论做了一个很具有启发性且清晰的解读,并充分肯定了“与孟子一起哲学”的诠释方法,然后他向萧教授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在“性之”哲学的框架下:(1)如何解释尧舜与汤武之间存在“性之”与“身之”“反之”的差异?(2)如何理解“心”与“性”的关系?(3)宋明理学很关注孟告之辨,如何看待朱熹对于陆九渊之死称“死了个告子”的评价?萧阳教授回答说他主要是把“性之”与“假之”作为两种不同的行动类型加以分析,“身之”“反之”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思考。他完全同意孟子以心论性的特点,对心所依据的原初现象已有一些初步想法,尚需进一步地完善,再行解说。“与孟子一起哲学”的诠释思路融合了朱、陆,既贯彻了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进路,又在分析的角度与朱熹相似,提倡回到原初现象去格物。
随后,深圳大学的郑宇健教授、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高山奎教授以及中山大学部分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萧阳教授进行了交流切磋,萧阳教授一一做了回答。讲座在热情洋溢的云端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