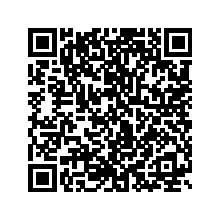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第四讲回顾 | 陈立胜:“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另一面向及其现代影响
2022年3月17日晚上七点,中山大学哲学系2021级研究生哲学前沿讲座系列第四讲“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另一面向及其现代影响”在锡昌堂103室举行,主讲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开场部分,陈少明老师首先介绍了陈立胜老师在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陈老师对儒家修身之学的研究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接着,陈少明老师指出儒家伦理观念当中的“孝”就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而陈立胜老师“家”哲学的另一面向无疑为我们理解“家”打开了另外一扇别样的大门。

讲座伊始,陈立胜老师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有关“要不要姓”“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家庭”之三问,联系近现代“家庭革命”当中“毁家”“破家”“去家”的反传统思潮,试图通过回顾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特征,回答“在一个视家如命的儒家文明中,革‘家’之命的意识形态究竟何以形成”这一问题。
继而,陈老师将讲座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近现代“家为万恶之源”的激进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回溯。其次梳理了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特征,又进而试图说明心学“家”观念与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当中所存在的连续与断裂。最后,陈老师就如何在现代性中安顿儒学“家”的观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思考。
在讲座第一部分,陈老师认为在由“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代”中,传统的家庭几乎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原罪”,成为源自于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穷追猛打的对象。“毁家”“破家”“去家”思潮与现代西方文明强行叩关是分不开的。在此当中,西方近代文化乃是由近代产业革命塑造的舍弃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毁家”“破家”“去家”的思潮正是中国由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方式向近现代产业革命过渡所掀起的思想浪花。然而,陈老师补充认为,近代“家庭革命”的思潮就其实际影响来说是有限度的。除此之外,陈老师亦指出,宗教信仰会因其超越世俗界的需要而与家庭一伦发生冲突。如果要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同质化的“想象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无论是普世的教会抑或是民族国家以及人间乌托邦,如何突破家庭一伦的限囿是不得不处理的难题。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陈立胜老师总结认为,与“家庭革命”相关的“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因为存在一定的局限,故而如张灏、王汎森等学者认为传统思想在近代中国自我人格与心态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理学中变化气质的工夫论与心学中的主体性之张扬为转型时期新人格的锻造、革命行动的决心与勇气之培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陈老师看来,阳明心学“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这一系列“家”观念的提出,均是由其“一体不容已”之仁学终极情怀而来。此“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被此“圣灵”所感动之先知先觉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身家之累”的限囿,并与“同志”(即被同一圣灵所感动者)结为一“会”、一“孔氏家”、一“道”“学”“政”三位一体的共同体。这一系列“家”观念为近现代中国“毁家”“破家”“去家”的“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凭借”,更在某种意义上为后者做出了“主题”上的铺垫工作,而“西方的冲击”则让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断裂”的特征。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陈老师回溯了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主要面向。陈老师认为,阳明心学一系“天下一家”的观念与“万物一体” 联系在一起, 二者共同构成心学一系“王道”观的核心命题。尤其在阳明晚年的论述当中,他强调“一体之仁”的“一体”与“无间”,“亲”字被不加区别地用于所有仁爱的对象:亲亲、亲人之亲、亲禽兽草木,天地万物均成为“一家之亲”的范畴(“莫不实有以亲之”“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皆有以亲之”), 这无疑充分体现了心学一系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精神旨趣。在陈老师看来,对治私欲是理学工夫论的一大论域,凡是膨胀无节的生理欲望以及由此衍生的名利心乃至生死一念都会被视为私欲的范畴。而“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是阳明与朱子对“止于至善”的共同理解。程朱理学通常会将人欲追溯到“身”这一环节:“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这跟老子“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理路是一致的。不过,与以上二者不同,心学一系还常将“家”视为私欲的一个源头。
陈老师指出,心学一系“家”哲学的特征次渐而出现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为“出家”辩护等五个方面。其中,“身家之私”的观点认为“破身家之私”是形成君臣相交形上学内涵(“天地交泰之象”)的先决条件(刘宗周)。第二,“身家之累”是指心学一系追求为己之学、了自家性命之学过程中时常遭遇到的生存问题。如王龙溪就说“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第三,心学一系惟道是求、惟心是求的精神旨趣不免产生“身家之私”与“身家之累”之感,由此可见其终极关怀者方是“家”,此“心”安处方是心学之家。第四,心学中人克服“身家之私”,化解“身家之累”,以其心安处为家,皆源自其日趋高涨的交友、结社以求道之需要。第五,友道的高涨,最终在心学一系中酝酿出为“出家”辩护的声音,如杨复所和李贽等人。由是,陈立胜老师认为,以上这些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中晚明白银经济兴起,交通网络日益改进,社会流动性日趋加速,科举考试所塑造的“ 远游求学”等密不可分。但归根结底,内在因素乃是中晚明“靡然成风”的讲学活动,因“共了性命”需要而建构的性命共同体,以及由此而透出和空前高涨的“成己”“成人”“成物”的淑世使命感。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陈老师分析了阳明心学一系“家”观念与“过渡时代”中的“毁家”“破家”“去家”思潮的关联性,详细分析了它在“数千年一大变局”中扮演的角色。陈老师认为,阳明心学一系的“家”观念不仅成为近现代“毁家”“破家”“去家”的精神“材料”“凭借”,而且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主题上的递进性与思维模式上的对应性。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主题上的递进性系指近现代的“毁家”“破家”“去家”思想是接续“万物一体”“天下一家”心学精神而演进的一个“结果”。种种突破“家界”而“成仁”的论述,它们的基调都是强调突破身家之私,强调仁爱之无所不通性,这皆可视为阳明心学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家国天下情怀的演进。只不过,比阳明心学一系“以天下为一家而不计自己之家”“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的论调相比,近代新仁学论述更加强调为了成全“大家”而不惜“杀身亡家”这一面向。
第二,都存在悟道现象。如王艮的托天之梦这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梦境很能体现出心学一系“万物一体、天下一家”成己、成人不二这一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此外,依《我史》所记,康有为的大同追求其精神动力也是源自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成一体,大放光明”的悟道体验。
然而,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以上的对应性,但是阳明心学与家庭革命中的“家”观点也呈现出四个显著的断裂:
第一,传统仁学之“通”是有根之“通”, 即在人伦共同体中,联属父母、兄弟、妻子,统会古人与后人,让天地生生不息的“仁意”“生机”自不容已地旁联纵贯于天下与万世之中。而新仁学之“通”则是一“横通”,且是一“无差别的横通”,即打破“中外”“男女”“上下”“人我”之彻底平等之“通”。
第二,尽管阳明心学一系注重友道,且有以友道涵化、调摄其他四伦的思想,但“友道”在根本上是乃“成全”而不是“取代”其他四伦。但在谭嗣同的新友道论述中,朋友一伦由涵化、调摄其他人伦之“首伦”递进为社会组织的唯一之伦,传统儒家的人伦社会一举被同质化的、清一色的、纯洁的友道共同体取代。
第三,在传统的身家之私与天下之公的论述中,公私是极富伸缩性的一对范畴,“公”与“私”的分际并无断裂为两橛,“公”领域是“私”领域的扩大与延伸。而在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公私论述中,“大公无私”成为一种基调,“一家之私”与“大群之公义”完全是一种零和关系。传统儒家独善其身、守道不回的隐退之路被截断,人于其家中自足存在的合理性被连根拔起。
第四,传统修身学中重要环节“齐家”与其上下一节“修身”“治国”皆被视为“无涉”,甚至被视为“不相容”。所谓仁学、修身学均将“家庭”一节截去,这在传统阳明心学是绝对不可设想的。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陈立胜老师基于“毁家”“破家”“去家”思潮所反映的由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遭遇的困境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在陈老师看来,社会生活的孤立化、原子化所造成的“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现代社会组织官僚化、形式化、人际关系的物化、去个人化所造成的“铁牢笼”(ironcage),个体与经济及政治的疏远所造成的“异化”(alienation),个体丧失了与他者可靠联系所造成的“失序”(anomie) 等等一系列所谓“现代性的隐忧”现象,本质上是现代个体作为“无负担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self)的“无家可归”。
就此,陈老师认为,如何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既让人之个体自由与尊严得到保障,又让人有“在家”的温暖感、亲切感与归属感是当今中西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金耀基曾指出今天中国文化面对的挑战就是要真正打通儒家文化设计的“第三条路”,而要打通此路则必须承认现代性中的个人生活世界已经从熟人社会(面对面的社群)进入到陌生人社会,因此必须把个人从“家”成员身份扩展为社会公民身份。在这个扩展身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家的集体中找回孔孟儒学所强调的个体的尊严与独立性,另一方面则要把传统家的亲和的人际间纽带扩大到社会中的陌生人上去。与此相关,杜维明先生则提出了“儒家社会”的道路,试图在“信赖社群”中达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之路。进而建成一个以“儒家‘为己之学’的精神内涵与‘自我实现’的道德律令为基础,且又有基于自由和权利的观念并发展保障公民隐私的法制”的儒家社会。
最后,陈老师指出,欲要践行上述所言的“儒家社会”的理想图景,必须重新恢复被“毁家”“破家”“去家”思潮所否定的“齐家”一节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激活“齐家”一节在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向阳明心学一系“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观念的一种“回归”,即在身—家—国—天下这一存有脉络中重建一种既能安顿个体自尊与自由又能保障人际和谐的社会秩序。除此之外,在陈老师看来,激活新世纪的齐家意识,需要一番系统而深入的理论阐释工夫。其中第一点就是要重新联通“家”(私域)与“社会”(公域)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关联性。第二,则需要重新阐述“家”存在向度的深刻精神内涵,比如中国传统观念当中“慈”的面向。
主持人陈少明老师总结认为,陈立胜老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且是比较严峻的考题,即我们如何理解儒家传统中他们理想的“家”。陈少明老师谈到,儒家的“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从孔孟到宋明理学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其次,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家”面临的前景究竟如何?陈少明老师指出,在陈立胜老师的报告当中,从阳明心学一系到近代对家的态度,都在试图追求排除家的障碍而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可能是某种道义的共同体,也可能是近代以来所倡导的“国家”。除此之外,陈老师亦认为,家的另外一个最小化的敌人可能是每一个个体。因为五四运动反家的概念当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个人自由主义,无论是巴金所写的《家》《春》《秋》,还是曹禺写的《家》。作品里面描写的都是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在这个家中受到了压迫,他们都要寻求某种意义上的解放,而不是为了想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在今天看来,“家”在现代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给家施加的压力,这在一些政治运动当中能够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现代关于个人权利问题的讨论当中。其中虽然没有明确说一个人用个人的要求反对家庭,但是在财产问题上则尤为明显。
在陈少明老师看来,家的精神生活跟它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需要做更进一步地讨论,因为这里涉及到究竟什么是家的问题?即家的定义问题。陈立胜老师最后把“家”定义为精神性的“心安”向度。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关系到家庭这一单位在社会秩序当中何以界定其位置?比如,无论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把家看作是障碍,还是在更小的个人意义上把家视为樊笼,他们都没有回答家原本的功能这一问题。从人类存续的角度上讲,家是维系人类存亡的最小单位。当然,家为每一个人情感以及道德感的培养提供了最基本的场所,换言之,它是情感孕育的源泉。最后,陈老师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伴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家庭是否依旧能够稳定?因为随着人与人的接触越来越广泛,加之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观念的普遍接受,一个人一生可能拥有不同的家庭,那么不同时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是更大意义上的家还是构成了对家的解体?这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陈立胜老师的报告无疑带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在提问环节,吴重庆老师分别就“家”到底是小农之家还是封建大家等问题与陈立胜老师进行了细致讨论,认为陈立胜老师的报告将革命与文明打通,把儒家伦理革命性的一面充分地展示了出来。阳明心学一系对“家”的认识,无疑进一步启发我们如何从纵通走向横通。陈老师也就同学们就江右学派当中是否存在“去家”倾向进行了解答,并指出阳明后学在“友道”一点上存有共通性。前沿哲学讲座第四讲至此圆满结束。
(供稿:张乾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