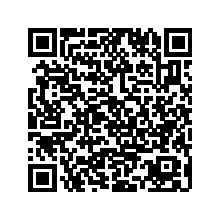郑辟瑞 | 感知中的“立义内容-立义”范式与所予的神话
作者简介:

郑辟瑞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郑辟瑞,江西井冈山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曾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译著《自身关系——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的思考与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1906-1907年讲座)》(商务印书馆,2016年)、《思想与自身存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等,在Husserl Studies、《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等中外文期刊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
【内容摘要】麦克道威尔将塞拉斯对所予的攻击和戴维森对“图式-内容”二元论的攻击等量齐观,一些胡塞尔学者也将胡塞尔的“立义内容-立义”范式作为“图式-内容”二元论的一种变样加以批判,并且坚持认为胡塞尔最终抛弃了这一范式。然而,对胡塞尔文本的考察表明,胡塞尔并未完全抛弃这一范式,这看起来证明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承诺了所予的神话。本文尝试通过阐释胡塞尔的后期文本,尤其是《被动综合分析》中关于“充实性的填料”和“非充实性的填料”的区分及其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学说,证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未陷入所予的神话,他的认识论使一种没有所予的神话的“图式-内容”二元论得以可能。
【关键词】胡塞尔、塞拉斯、“立义内容-立义”范式、所予的神话、填料
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为哲学贡献了一个魔力词:所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所予的神话”这个词不仅标识了一个哲学论题,也标识了一个重要的标准,以至于一些学者用来衡量经典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思想有效性。比如,康德哲学是塞拉斯思想的主要来源,塞拉斯的“所予的神话”作为标准也被用来反哺当代的康德研究。[1]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得到相应的考虑,于是,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现象学陷入了所予的神话之中吗?或者更具体地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承诺了所予的神话吗?
一、一种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
答案常常是肯定的。人们普遍认为,胡塞尔超越论的现象学几乎必然会陷入“所予的神话”,因为它主张,私人思想的意向性比公共话语的意向性更加本原,由此令人误解地颠倒了私人思想与公共语言的奠基关系。用当代“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代表人物布拉西耶(Ray Brassier)的话来说,“意义植根于日常的‘赋义’意识行为之中,这一主张导致现象学,至少它的超越论变体,直接陷入神话。”[2]在这一语境中,布拉西耶明确提及胡塞尔,“对日常意向性姿态——如胡塞尔和福多那般不同的哲学家都具有的一种姿态——的拒斥是放弃所予的神话的另一个直接后果”[3],因而,“意向性”与“所予的神话”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布拉西耶用“私人性/公共性”这一对概念来解释“所予的神话”,陈嘉明也在类似的意义上批评胡塞尔。在引用了塞拉斯的话,“即使像有关颜色的那些‘简单’概念,也是一个长期的在公共场景中对公共对象(包括言语行为)的被公共地强化的反应过程的结果”[4]之后,他解释说,塞拉斯在这里连续使用了三个“公共”,以便强调语言和概念的“公共性”,“是由于塞拉斯看到了感知作为一种个人的‘内在事件’的‘私人性’问题,而将它与‘主体间性’、一种公共性相结合的结果。在上句引语中,它表现为个人感知中渗透着的概念和语言的‘公共性’。这些观点对于分析胡塞尔的‘所予性’学说当有启发性,胡塞尔缺乏的正是公共性之维。”[5]在陈嘉明看来,胡塞尔的直观原则,即直观是一切合理性的最终来源,必然会使得胡塞尔的现象学陷入所予的神话,这是因为,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直观中已然渗透了概念因素,而概念因素则来自公共话语。
无论是布拉西耶还是陈嘉明,他们都是从“私人性/公共性”的奠基秩序的角度来刻画所予的神话,这一角度显然是和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深远的“私人语言论证”息息相关的。这一思路当然可以在塞拉斯的文本,尤其是影响最大的伦敦讲座“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获得不少的支持,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塞拉斯持有的“心理学的唯名论(psychological nominalism)”。在一段反复为人所引用的段落中,塞拉斯这样界定心理学的唯名论:
据此,所有关于分类、相似、事实等的觉知,总之,所有关于抽象实体的觉知——确切地讲,甚至所有关于殊相的觉知——都是语言的事。据此,习得使用一种语言的过程甚至都不预设觉知关乎所谓的直观经验的分类、相似和事实。[6]
概念的形成并非通过对直观经验的比较和抽象而来,恰恰相反,直观经验预设了对相关概念的掌握。因而,导致所予的神话的一个根源是,我们默认了学习语言的人天生对逻辑空间有所觉知,而学习语言的过程无非是通过将此逻辑空间中的要素与语言符号联系起来,以便将已有的对此逻辑空间的觉知明晰化。然而,塞拉斯也明确指出,“虽然这个想法的确是神话最普遍的形式,但远非其根本。”[7]在与上述陈嘉明关于“公共性”几乎同样意义上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塞拉斯也连续使用了三个“公共”,以突出学习语言的公共性——之后,塞拉斯指出,诉诸公共性/私人性的对立,充其量可以避免陷入感觉材料论的神话,但并不能避免“看上去(looks)”的神话,因为这里并不谈及私人的感觉材料,而是恰恰谈及公共的物理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塞拉斯的“所予的神话”并非与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完全重合。
此外,胡塞尔甚至在理论上也并未陷入“公共性/私人性”版本的所予神话。与陈嘉明的批评相反,胡塞尔坚持认为,感知经验是概念行为。不同于感觉,感知作为意向行为已然包含了概念内容,用胡塞尔自己的术语来表达,即质性(Qualität)和质料(Materie),尤其是质料,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被称为立义意义。不同于意向行为中的第三种成分“描述内容”,质性和质料两者构成了意向行为的意向本质。在其后期著作《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感知经验与判断交织在一起,在此,我们满足于引用胡塞尔一段常被引用的话:
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进行认识-判断活动的世界,一切成为可能判断之基底的东西从中刺激着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确总是已经作为混有逻辑作用的积淀物的世界而被预先给予我们了的;它从来不是以别的方式给予我们的,而只是作为我们或他人已经对之进行了逻辑判断、认识活动的世界而给予我们的,这些他人的经验成果我们可以通过传达、学习和传统而接受过来。[8]
概念化的世界已然预先被给予了我们。
二、所予的神话与“图式-内容”二元论
塞拉斯并不否认胡塞尔思想对他的影响,在其“自传性反思”中,塞拉斯明确指出,是现象学家马尔文·法伯(Marvin Farber)引导他接触到胡塞尔,法伯对胡塞尔思想的自然主义解释对于他自己后来的哲学策略来说具有关键性的影响。[9]塞拉斯的说法绝非虚言,尽管他并没有关于胡塞尔的专门研究,但是他对胡塞尔思想的讨论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生涯。早至他的最初几篇论文之一“实在论与新的语词道路”[10]中,塞拉斯提及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评,但是认为,胡塞尔仍然陷入了认知主义。晚至他的“诺特丹讲座”中,胡塞尔被他当作一种典型的感知理论代表而加以评判。[11]熟悉胡塞尔思想的人,在读到塞拉斯文本中出现的“悬搁”、“还原”这些打上胡塞尔烙印的术语时,总会会心一笑的。
不过,塞拉斯似乎从未明确地将对胡塞尔思想的讨论放在“所予的神话”这个标题之下,并以此为标准来考虑胡塞尔的思想,这一点使得我们要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胡塞尔的现象学承诺了所予的神话吗?”,就显得有些困难了,我们还不知道应当从哪个思想的角度切入胡塞尔与塞拉斯的关系之中。
在此,或许我们可以引入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的一个说法,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一说法是有启发性的,即,“塞拉斯对所予的攻击以我在第一讲中所利用的那种方式对应于戴维森对他所称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概念图式和经验‘内容’的二元论——的攻击。”[12]如果麦克道威尔的说法成立,而胡塞尔恰恰常在“立义内容-立义”范式(Auffassungsinhalt-Auffassung Schema)的名称下被视为“图式-内容”二元论(the dualism of scheme-content)的持有者,那么,胡塞尔似乎也因而必然陷入了所予的神话。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第三种选项,即,没有所予的神话的“图式-内容”二元论。本文尝试将胡塞尔和塞拉斯联系起来,以便提出这一选项。
让我们从“所予的神话”开始。
虽然在1956年的“伦敦讲座”一开篇,塞拉斯就明确主张,本讲座意在“总体批判整个所予框架”[13],而对感觉材料理论的批评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但是,在整个讲座中,甚至可以说在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所有思考中,他都总是只谈及这一神话的“最普遍的形式”、“根源”、“形式之一”、“最简明形式”、“核心”、“另一表达”以及“最基本的形式”[14]等,却几乎从未给出对所予的神话本身的明确规定,而总是借助批评具体形式的所予来展开,这也就使得人们能够谈及不同版本的所予的神话,却无法给出所予的神话的定义。
不过,在塞拉斯的文本中有一个例外。伦敦讲座20年之后,塞拉斯回顾到,“所予的神话,正如我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所定义的那样,就是如下观念,即,对象自身呈现给我们作为是某种种类,或者某种类型。”[15]如果塞拉斯是严肃的,那么或许他想到的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第26节,在那里,他将所予的神话描述为,“实际上,这个方面的所予神话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取决于其他的哲学承诺。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想法:觉知有些分类——我用‘分类’来首先想到确定的感觉可重复项——是‘直接经验’的一个原始的、毫无疑问的特征。”[16]在此,塞拉斯针对的是传统经验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感觉和思想。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第7节中,塞拉斯将这两种内在片段描述为:
(1)这个想法,即存在某些内在片断——例如,关于红或关于C#的感觉,没有任何在先的学习或概念生成过程,它们也能发生在人类(和野兽)身上;没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可能看到(例如)一个物理对象的向面表面是红的和三角形的,或听到某一物理声音是C# 。
(2)这个想法,即存在某些内在片断,它们是非推论地认识到某些项是(例如)红的或C#;这些片断给所有其他经验命题提供证据,是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17]
在感觉材料理论家的构想中,这些基础的内在片段需要同时具有两种特征,以便能够扮演基础性的和辩护的角色:一方面,这些内在片段是基础性的,因为它们是直接被给予的,无需在先的习得或者构想;另一方面,这些内在片段是辩护性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命题知识。
但是,事实上,这两种特征相互并不一致,感觉很难称得上是认识论的,它们只有因果效用。为了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内在片段必须能够进入辩护的秩序,或者用塞拉斯的术语来说,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因果要素不能用来辩护,它们也不能用来构成知识。在这种意义上,麦克道威尔说,“感觉看起来则像是空转的惰轮”[18],它毫无用处。
情况似乎证实了麦克道威尔上述的类比,也就是说,我们避免所予的神话,是通过将感觉排除出认知事实,而这恰恰是与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图式-内容”二元论的攻击一致的。
戴维森所攻击的“图式-内容”二元论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名称,尽管如此,人们普遍承认,“图式-内容”二元论在近现代哲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戴维森所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于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图像已经规定了现代哲学认为它必须解读的诸多问题。”[19]不难看出,这一“图式-内容”二元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正是康德,更进一步说,它表达了康德著名的话:“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结合这一康德式的背景,麦克道威尔认为,“图式-内容”二元论更好的表达是“图式与所予的二元论”,在其中,图式指的是“概念图式”,“所予”则对应于直观,表示“经验接纳的片段”,于是,“图式-所予”二元论所表达的是,心智片段中包含的概念内容(图式)和非概念内容(所予)在意向性(或者更具体来说,知识)的构成中各自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予提供内容,概念则赋予其形式,对其进行构造或者解释。套用康德的言说模式,刘易斯(C. I. Lewis)总结到:“如果没有材料给予心灵,那么知识必然是缺乏内容和任意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它必然对之为真的。而如果没有心灵自身施加的解释或者构造,那么思想就变得多余,错误的可能性变得不可解释,真假的区分有变得无意义的危险。”[20]而对于戴维森来说,包括感觉在内的所予并不能为信念做出辩护,正如他所坚持的,“除了另一个信念,没有什么能够算得上是持有一个信念的理由”[21],这样,因为其非概念性,感觉就被排除出理性的关系之外了。
三、胡塞尔的“立义内容-立义”范式
然而,令麦克道威尔感到困惑的是(而这当然并非塞拉斯本人的观点),塞拉斯逐渐放弃了他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的康德式洞见,即,将感知经验刻画为“含有命题断言”[22],他将非概念的感觉从前门踢出去,又将它从后门迎了回来。
出于同样的理由,波姆(Rudolf Boehm)认同胡塞尔放弃“图式-内容”二元论,或者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立义内容-立义”范式。
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胡塞尔用来表达“图式-内容”二元论的术语各不相同,不过,人们通常谈及“立义内容-立义”范式,这是因为胡塞尔自己是在这一名称之下来批判这一构想的:“并不是每个构造都具有立义内容-立义这个范式。”[23]尽管胡塞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但是作为典型和最常用的概念,“立义内容”和“立义”分别指代意向行为中非概念性和概念性的内容。
围绕胡塞尔是否抛弃了“立义内容-立义”范式,胡塞尔学者之间有着长期而复杂的争论。
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编者引论”中,波姆指出,可能是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第一个指出“立义内容-立义”范式对于胡塞尔意向分析来说具有的重要意义,“胡塞尔……长期以来根据立义-内容的范式而将意识或意义给予定义为‘赋予灵魂的立义’。当他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认识到,这种功能是以另一种更深层的功能为前提的,在此更深的功能中,内容预先对立义构成自身,这时他也就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4]梅洛-庞蒂似乎表明,胡塞尔发现,立义内容与立义的区分并不适用于更为根本的时间意识现象领域,基于此,他最终抛弃了“立义内容-立义”范式。
近来,一些胡塞尔学者试图表明,胡塞尔从未完全抛弃“立义内容-立义”范式,他只是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本文无意于介入其中的争论,我们满足于指出,那些赞同相反观点——即胡塞尔从未放弃这一图式——的人能够在胡塞尔后期著作中找到更多的文本支持,比如,在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分析”讲座中,他仍然坚持:
所有这些意向相关项的要素——我们在意向相关项的观点中指向对象并把它们看作对象上的要素——都是借助内在的感觉素材和那个彷佛赋予它们以灵魂的意识而被构造起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把立义看作超越的统觉,超越的统觉恰恰标明意识成就,这种意识成就赋予感性素材之纯粹的内在内涵、亦即所谓的感觉素材或原素性的素材之纯粹的内在内涵以展示客观的‘客观之物’的功能。[25]
这段引文也很好地表明了胡塞尔在“立义内容-立义”范式有效性上的连续立场,它将胡塞尔在不同时期使用的术语统统纳入进来,比如“感觉素材”、“赋予灵魂”、“立义”和“统觉”是《逻辑研究》中常用的术语,而“意向相关项”、“原素性的素材”这些术语则显然带有《观念1》的印记。
如果胡塞尔最终并未放弃“立义内容-立义”范式,因而并未放弃“图式-内容”二元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胡塞尔的现象学承诺了所予的神话?在我们看来,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引入动态的内容-同一性理论,我们能够说明,胡塞尔如何“认为经验除了包含断言还需要感觉作为另一个元素?”[26]
我曾经在“胡塞尔是概念论者吗?——重读胡塞尔的第六逻辑研究”[27]一文中建议,围绕着“感知经验是否具有概念内容”的问题,在胡塞尔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区分出意向性论题和认识论论题。我进一步主张,我们可以将从《逻辑研究》“第五研究”向“第六研究”的过渡视为从意向性论题向认识论论题的转移。第五研究中意向分析所讨论的一些主题在认识论的语境中得到重新构造,比如,客体化行为领域就以新的方式被刻画为认识的“起源地”[28]。
与之相应,客体化行为的成分,尤其是感觉内容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名称上也有着相应的改变。在第五逻辑研究中,感觉内容被称为“描述内容”,以区别于对于意向行为具有构造性的意向内容(它包括质性和质料),而描述内容是纯粹描述心理学分析的课题,它被体验,并且有待“立义”或者“统摄”,或者用胡塞尔形象的话来说,有待“被赋予灵魂”,而描述内容本身是不具有构造性功能的。在第六逻辑研究中,用来刻画“感觉内容”的名称主要有“充盈(Fülle)”、“代现性内容(repräsentierender Inhalt)”和“被代现者(Repräsentant)”。借助于对认识的作用,充盈在与概念内容的关系中就不再是纯粹惰性的,而是“以补充的方式特别从属于质料”[29],充盈不再是完整的意向行为中与质性和质料单纯排列在一起的第三种因素,而是和完整的质料一道构成直观的直观内容。将感觉内容称为“代现性内容”,这也表明了,感觉内容本身的差异也对意向行为的类型以及认识的构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代现性内容的不同功能规定了不同类型的意向行为。
将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作为模板,胡塞尔将具体的客体化行为分为三类,即,纯粹直观行为、纯粹符号行为和混合行为。这三类行为作为具体的客体化行为都具有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质性、质料和代现性内容,这些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代现性内容在它们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在纯粹直观行为中,代现性内容作为直观行为的承载者,它是“直观代现性的内容”。在纯粹符号行为中,代现性内容作为符号行为的承载者,它是“符号代现性的内容”,而混合行为的特征则是:
它具有这样一个代现性的内容,就被表象的对象性的一个部分而言,这个内容是作为映像的或自身展示的被代现者起作用,而就那个补充部分而言,它是作为单纯的指向在起作用。[30]
混合行为的代现性内容同时起到直观代现和符号代现的作用。
直观代现性的内容和质料有着本质的内在关系,包含这两个组成成分的直观行为能够充实,或者说,辩护相关的符号行为,这样,直观代现性的内容通过与质料的结合,或者说通过概念化,而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符号代现性的内容和质料有着偶然的外在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不同于描述内容,因为符号代现是以相邻性的方式进行的。
纯粹符号行为和纯粹直观行为都是极限状况,具体的客体化行为大多数是混合行为。外感知就是典型的混合行为,它混合了意向和充实这两种视角。在外感知中,代现性内容一部分作为直观行为的载者起作用,从而充实了在先的意向,另一部分则作为符号行为的载者起作用,从而引发有待充实的意向。
四、充实性的填料与非充实性的填料
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胡塞尔似乎认为,在混合行为中,代现性内容同时作为符号代现性内容和直观代现性内容起作用,它所包含的符号代现和直观代现“是在与同一个意向本质的联系中”[31]。而在“被动综合分析”讲座——这应该是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之后少有的几份文本,在其中,胡塞尔再一次以“充实”为主题做出集中的说明——中,胡塞尔将混合行为中的这两种代现性内容成分,即直观代现性的内容和符号代现性的内容,称为充实性的填料(erfüllendes Füllsel)和非充实性的填料或者单纯的填料(bloßes Füllsel)。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直观化方式:澄清性的直观化和证验性的直观化,即意向充实。澄清性的直观化只是对相关空乏意向的单纯描绘,比如我们可以以图像的方式描绘我们的空乏期待或者过去的图景;意向充实则是指,空乏的意向与一个相应的直观行为进入相合的综合,对象就像它被意指的那样在直观中自身给予。胡塞尔有时也将两者分别称为“非自身给予的直观”和“自身给予的直观”,而在空乏表象方面与之对应的是“滞留与前摄……之间的区别。”[3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滞留与前摄作为空乏表象的两种直观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前摄方面,两种直观化是可分离的,对期待意向的澄清并不是,并且也总尚未是对此意向的充实,毫无疑问,意向与充实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间距;在滞留方面,情况则相反,两种直观化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澄清和充实性的证验在这里不应被分开,每一个直观化的综合在此都必须先天地成就二者。”[33]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前摄不同,“滞留——就像它们在其原初性中出现那样——没有意向的特征。”[34]在滞留的变异中,直观在不断消逝,素朴的感知意向是朝向未来的,滞留要获得意向特征,则需要一个事后返回朝向的联想。基于此,对滞留的澄清,或者说对滞留的直观化澄清已然是再回忆意向的充实。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胡塞尔谈及充实性的填料与非充实性的填料之间的区分,它们的区分依赖于相应的空乏表象。比如,我们回忆过去所认识的某个人,非直观的回忆在直观性的再回忆中得到充实。我们的回忆图像中突出出来所忆人物的络腮胡须、眼镜这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当然起到充实性的作用。然而,具体的回忆图像中,胡须与眼睛毕竟具有具体的颜色,这些颜色并不起到充实性的作用,它们只是单纯的填料,是超出了充实功能之外的剩余。
但是,另一方面,胡塞尔也说:“只要直观还包含不确定性或单纯的填料,这种满足就仍只是一种相对的满足,就留有剩余的不满足。”[35]也就是说,单纯的填料可以转变为充实性直观,“在此超出预示、超出确定的被期待物而出现的东西不是单纯地被标识为填料,而是被标识为切近规定。但这种切近规定本身具有充实的特征。”[36]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理性都同时是实践理性,空乏表象与相应直观之间不仅仅是静态的理论关联,而且从发生的视角来看,空乏表象总是有待充实的表象,它包含着一种追求,去谋求满足,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充实/满足相互交织,这正是这种对满足的追求,从而使得作为单纯填料的感觉内容能够起到充实功能,并且凝聚为意向内容。事实上,意指所追求的存在者自身依赖于意指本身的变化,正如感知作为存在者的自身被给予,它必然包含意指,而非单纯的展现,“感知是切身地观视和拥有对象自身。……对象……是作为它自身——就像它被意指那样——被给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亲身站在那里。”[37]对象自身是如其被意指那样给予感知的对象自身。借助于上述“回忆人物”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在代现性内容中,所忆人物的络腮胡须、眼镜这些特征是直观行为的载者,它们起到充实性的作用,而胡须与眼睛的具体颜色一方面作为单纯的填料,引发新的更为确定的意指,这一意指关系到胡须与眼睛的具体颜色,由此,如其被意指的对象本身也获得了切近规定,因而需要在进一步的感知中获得充实,而这一过程原则上是无限的。
五、没有所予的神话的“图式-内容”二元论?
在“胡塞尔是概念论者吗?——重读胡塞尔的第六逻辑研究”一文中,[38]我主张,胡塞尔持有一种动态的内容-同一性理论,据此,概念内容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充实中的直观行为和符号行为偶然地具有同一概念内容,毋宁说,在动态的充实过程中,直观行为获得概念内容,这一概念内容是从符号行为那里流渡(Überfließen)到直观之中,以至于两个行为具有同一概念内容。为此,我们应该区分符号行为之前和之后的直观行为,前符号的直观行为扮演引起联想的角色,即引起概念响应的因果角色,而后符号的直观行为能够反过来充实符号行为,因而能够扮演辩护的角色。
我把胡塞尔的动态的内容同一性理论视为塞拉斯式的“事后辩护(ex post facto justification)”(用布兰顿的话来说)[39],也就是说,借助于“通过回忆而构造性地误认”[40]的辩护的一种先行版本,和塞拉斯意义上的回忆一样,混合行为的代现性内容以曲折的或者循环的方式扮演了联想和辩护这两种角色。
麦克道威尔看起来也认同塞拉斯式的“事后辩护”。与戴维森不同,麦克道威尔强调经验与信念的区分,并且认为,经验能够借助于它们的概念内容而扮演给予相关信念以理由的角色,但这恰恰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信念。不过,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着细微的差别。对于塞拉斯来说,这种“事后辩护”也是概念化“过去的事实,人们在它发生时并未,或者甚至……不能将它概念化”[41],也就是说,过去的经验本身并没有概念内容;麦克道威尔则坚持彻底的概念论立场,在他看来,“一个知觉经验的内容已然是概念性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并非引入了一种新的内容,而只是认可了那个它在其上得到奠基的经验已然具有的那个概念内容(或者其中的一个部分)。”[42]对于塞拉斯来说,概念化的操作机制是“误认(mistaking)”,而对于麦克道威尔来说,这一操作机制则是从经验中已然是概念性的内容之中进行的相关选择。尽管如此,塞拉斯,因而胡塞尔仍然能够保留非概念内容,从而提出一种没有所予的神话的概念(图式)-非概念(内容)的二元论。
[1] 比如,这一思路影响到了当代的康德研究,参Watkins, Eric, “Kant and the Myth of the Given”, in Inquiry 51.5 (2008), pp.512-531; “Kant, Sellars, and the Myth of the Given”, in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43.3 (2012), pp.311-326。
[2] Ray Brassier, “Nominalism, Naturalism, and Materialism: Sellars’s Critical Ontolog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edited by Bana Bashour and Hans D. Muller (Routledge, 2014), p.105.
[3] Ray Brassier, “Nominalism, Naturalism, and Materialism: Sellars’s Critical Ontolog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p.105.
[4]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7. 转引自陈嘉明,<意识现象、所予性与本质直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有关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1(2012),页52。
[5] 陈嘉明,<意识现象、所予性与本质直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有关质疑>,页52。
[6]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页51。
[7]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27。
[8] 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编,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页59。
[9] 参Wilfrid Sellar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in Action, Knowledge and Reality: Crit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ilfrid Sellars, edited by H. N. Castañed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5), pp.277-293.
[10] 参Wifrid Sellars, Pure Pragmatics and Possible Worlds: The Early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effrey F. Sicha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2005), p.134, note 3.
[11] 参Wilfrid Sellars, Notre Dame Lectures 1969-1986,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edro V, Amaral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2015),p.234。
[12] 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新译本),韩林合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页7。
[13]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12。
[14] 分别参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26,52,56,59,62,90和Wilfrid Sellars, “The Lever of Archimedes”, in In the Space of Reasons: Selected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edited by Kevin Scharp and Robert B, Brando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37.
[15] Wilfrid Sellars, Kant and Pre-Kantian Themes: Lectures by Wilfrid Sellars, edited by P. V. Amaral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84.
[16]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47-48。
[17]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17-18。
[18] 约翰·麦克道威尔,《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页14。
[19] Donald Davidson, “The Myth of the Subjective”, in 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edited by Michael Krausz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1; 刘易斯有类似的说法,“承认这一事实,这是其中一个最古老,也最普遍的哲学洞见了。”(C. I. Lewis, Mind and The World-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 (Dover Publications, 1929, 1956), p.38)
[20] C. I. Lewis, Mind and The World-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 pp.38-39.
[21] Donald Davidson,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edited by Ernest LePor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6), p.310.
[22]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32。
[23]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37。
[24] Maurice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Gallimard, 1945), p.178, note1 ; 译文引自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页23,注释1。
[25]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30。
[26] 约翰·麦克道威尔,《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孙宁译,页113-114。这个问题是麦克道威尔给塞拉斯提出的,我们借以用来向胡塞尔提出同样的问题。
[27] 参拙文, “Is Husserl a Conceptualist? Re-reading Husserl’s sixth 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35.3 (2019), pp.249-263.
[28]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页50。
[29]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页67。
[30]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页87。
[31]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页88。
[32]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18。
[33]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04。
[34]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00。
[35]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07。
[36]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03。
[37] 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页121。
[38] 参拙文, “Is Husserl a Conceptualist? Re-reading Husserl’s sixth 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35.3 (2019), pp.249-263.
[39] Robert Brandom, “Perception and Rational Constraint”,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8.2 (1998), p.376; 布兰顿用这个词来说明塞拉斯的这段话,“琼斯现在认识到(因而记得)这些具体事实确曾存在。它不要求这样是正确的:他在这些事实存在时认识到它们存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页62。)
[40] Rebecca Kukla, “Myth, Memory and Misrecognition in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1 (2000), p.202.
[41]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63, 1991), p.170, note13. 这是塞拉斯于1963年补充的注释,这个注释以及其他几个补充的注释没有出现在单行本中。
[42] 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新译本),韩林合译,页75。
参考文献
陈嘉明,<意识现象、所予性与本质直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有关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1(2012):42-56。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编,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新译本),韩林合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孙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美)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Brassier, Ray. “Nominalism, Naturalism, and Materialism: Sellars’s Critical Ontolog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Ed. by Bana Bashour and Hans D. Muller, Routledge, 2014.
Brandom, Robert. “Perception and Rational Constrai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8.2 (1998): 369-374.
Davidson, Donald. “The Myth of the Subjective”, in 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Ed. by Michael Krausz,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son, Donald.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Ed. by Ernest LePor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6.
Kukla, Rebecca. “Myth, Memory and Misrecognition in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1 (2000): 161-211.
Lewis, C. I.. Mind and The World-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 Dover Publications, 1929, 1956.
Sellars, Wilfrid.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ellars, Wilfrid.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in Action, Knowledge and Reality: Crit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ilfrid Sellars. Ed. by H. N. Castañed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5.
Sellars, Wilfrid. Pure Pragmatics and Possible Worlds: The Early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Ed. and Intr. by Jeffrey F. Sicha.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2005.
Sellars, Wilfrid. “The Lever of Archimedes”, in In the Space of Reasons: Selected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Ed. by Kevin Scharp and Robert B, Brando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ellars, Wilfrid. Kant and Pre-Kantian Themes: Lectures by Wilfrid Sellars. Ed. by P. V. Amaral.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Sellars, Wilfrid.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63, 1991.
Watkins, Eric. “Kant and the Myth of the Given”, Inquiry 51.5 (2008): 512-531.
Watkins, Eric. “Kant, Sellars, and the Myth of the Given”,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43.3 (2012): 311-326.
Zheng, Pirui. “Is Husserl a Conceptualist? Re-reading Husserl’s sixth Logical Investigation”, Husserl Studies 35.3 (2019): 249-263.
【本文原载于《哲学与文化》总第5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