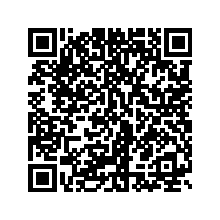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第四讲回顾|方向红:为何“长女”“寡发”“多白眼”——对《周易》分类方法的现象学考察与反思
2021年3月24日晚上七点,方向红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801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报告题目为“为何‘长女’‘寡发’‘多白眼’——对《周易》分类方法的现象学考察与反思”。
报告由陈少明教授主持。陈教授介绍说,方教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既不是对哲学概念格义式的比较研究,也不是对中学西传或者西学东渐的哲学史研究,而是对中国哲学中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对周易原理的研究。

方教授首先感谢了陈少明教授的介绍,并且欢迎了同学们的到场。方教授从福柯的《词与物》中摘录了一段话,这段话表达了福柯在遭遇中国古代分类系统时所感受到的震惊和由这种不可思议带来的大笑。也就是说,即使在后现代的解构语境下,中华文明依然能够让西方最宽容的哲学家们也感受到思考的“边界”。
方教授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警惕。对于研究易学而言,如果我们认定《易经》干脆就是迷信的或者是前科学的,那么这至少有悖于福柯的诊断;但是如果我们认定《易经》早已经摆脱了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那么这是一种不真诚,而且最终也是文明上不自信的体现。
方教授认为,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关于分类的标准。首先,分类要和主体个人的兴趣爱好无关;其次,分类一定要刚好把整体分完,既不多也不少。胡塞尔向我们提供了形式化与总体化的划界模式,并且向我们揭示出整体一定会大于、高于部分之和的现象;海德格尔在晚期用天地人神的方式完美地对“物”进行了划分;马里翁从绝对的内在性出发,向我们揭示了严格的现象只能根据现象自身给出自身。
带着这些现象学明察,方教授开始了对《易经》的探索。如果我们从属性的角度来看,“长女”、“寡发”和“翻白眼”分别属于家庭地位、毛发和眼睛,是完全不相干的三件事。但是,《易传》凭什么能够认为这些象是一类的呢?难道这些不是比附和联想吗?与自然态度的解释不同,方教授认为,取象比类或者从经验中抽象并不是八卦的来源。中国古代的圣人发现,分类完全可以从运动入手,世界可以分为动和静,比如阴表示不动、静止,阳表示动,世界一下子就被划分出来了。
同理,一定是先贤们发现了有八种先天的运动,用八卦来表示,人们才能凭借八种先天的运动来对经验世界中的运动进行分类。这些发现,并不是某种现象学的“引申和发挥”,我们在邵雍的《皇极经世》中可以看到,现象学的考察恰恰暗合于邵雍的思路。
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区分先天与后天、先验与经验以及生成与动力。这三组概念中的前者,是非-经验的,还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出现;而这三组概念中的后者,描述的则是这个现实、具体的世界。
不仅如此,方教授还指出,任何一种对《易经》先天原理的解说都可以在后天世界比如中医中去验证自己,这样我们便可以时刻校正自己,以免我们的阐释陷入玄想。
陈少明教授对本场报告作了总结,他认为,本场报告非常符合哲学前沿的课程主题,前沿指的未必是提出了新的和前所未有的问题,而是对根源性的问题有所思考。最后,本场报告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供稿:张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