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思想摆渡”系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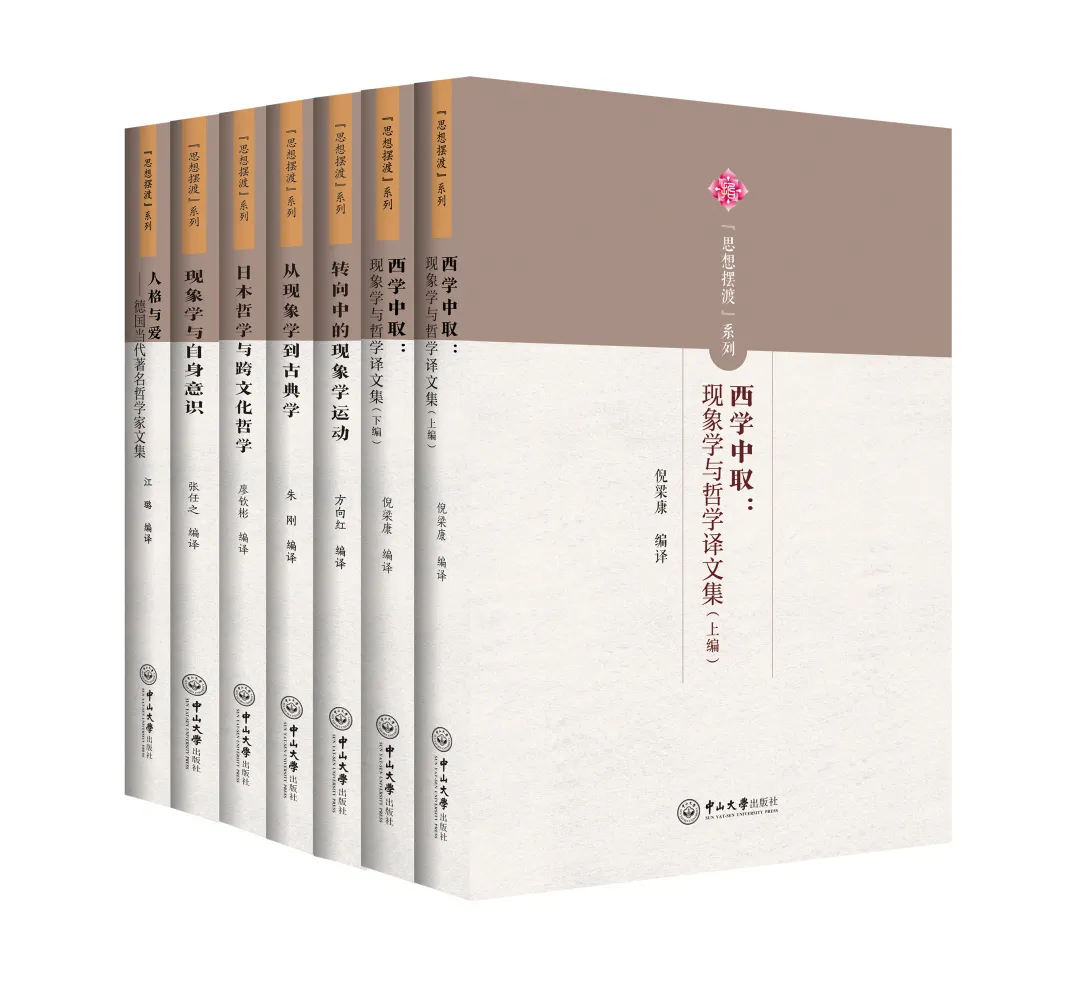
“思想摆渡”系列
总序
一条大河,两岸思想,两岸说着不同语言的思想。
一岸之思想如何摆渡至另一岸?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谁推动了思想的摆渡?第二,思想可以不走样地摆渡过河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普遍的观点是,正是译者或者社会历史的某种需要推动了思想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例如,某个译者的眼光和行动推动了一部译作的问世,某个历史事件、某种社会风尚促成了一批译作的问世。可是,如果我们随倪梁康先生把翻译大致做“技术类”、“文学类”和“思想类”的区分,那么,也许我们会同意德里达的说法,思想类翻译的动力来自思想自身的呼请“请翻我吧”,或者说“渡我吧”,因为我不该被遗忘,因为我必须继续生存,我必须重生,在另一个空间与他者邂逅。被思想召唤着甚或“胁迫”着去翻译,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译者们的表述。
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几乎不会有人天真地做出肯定回答了,但大家对于走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例如,有人坚持字面直译,有人提倡诠释式翻译,有人声称翻译即背叛。与这些回答相对,德里达一方面认为,翻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走样是不可能的,走样的程度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以至于思想自身在吁请翻译的同时发出恳求:“请不要翻我吧。”在德里达看来,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的翻译不仅会面临另一种语言中的符号带来的新的意义链的生产和流动,更严重的是还会面临这种语言系统在总体上的规制,在意义的无法追踪的、无限的延异中思想随时都有失去自身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成了一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事情。
如此一来,翻译成了不可能的可能、没有必要的必要。思想的摆渡究竟要如何进行?若想回应这个难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思想是如何发生和传播的?它和语言的关系如何?让我们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两个问题做点思考。我们从第二个问题开始。众所周知,自古希腊哲学开始,思想和语言(当然还有存在)的同一性就已确立并得到了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坚持和贯彻。在现象学这里,初看起来,各个哲学家的观点似乎略有不同。胡塞尔把思想和语言的同一性关系转换为意义和表达的交织性关系。他在《观念I》中就曾明确指出,表达不是某种类似于涂在物品上的油漆或像穿在它上面的一件衣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言语的声音与意义是源初地交织在一起的。胡塞尔的这个观点一直到其晚年的《几何学的起源》中仍未改变。海德格尔则直接把思想与语言的同一性跟思与诗的同一性画上了等号。在德里达的眼里,任何把思想与语言区分开并将其中的一个置于另一个之先的做法都属于某种形式的中心主义,都必须遭到解构。在梅洛-庞蒂看来,言语不能被看作单纯思维的外壳,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定位在表达着的身体上。为什么同为现象学家,有的承认思想与语言的同一性,有的仅仅认可思想与语言的交织性呢?
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其实源于思考语言的视角。当胡塞尔从日常语言的角度考察意义和表达的关系时,他看到的是思想与语言的交织性;可当他探讨纯粹逻辑句法的可能性时,他倚重的反而是作为意向性的我思维度。在海德格尔那里,思的发生来自存在的呼声或抛掷,而语言又是存在的家园。因此,思想和语言在存在论上必然具有同一性,但在非本真的生存中领会与解释却并不具有同一性,不过,它们的交织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领会则解释无处“植根”,没有解释则领会无以“成形”。解构主义视思想和语言的交织为理所当然,但当德里达晚期把解构主义推进到“过先验论”的层面时,他自认为他的先验论比胡塞尔走得更远更彻底,在那里,思想和句法、理念和准则尚未分裂为二。在梅洛-庞蒂的文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失语症患者由于失去思想与言语的交织性而带来的各种症状,也可以看到在身体知觉中思想与语言的同一性发生,因为语言和对语言的意识须臾不可分离。
也许,我们可以把与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称为普通语言,把与思想同一的语言称为“纯语言”(本雅明语)。各民族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非本真的生存论语言等都属于普通语言,而纯粹逻辑句法、本真的生存论语言、“过先验论”语言以及身体的表达性都属于“纯语言”。在对语言做了这样的划分之后,上述现象学家的种种分歧也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了。很明显,作为“纯语言”的语言涉及思想的发生,而作为普通语言的语言则与思想的传播密切相关。我们这里尝试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出发对思想的发生做个描述。首先需要辩护的一点是,以身体为支点探讨“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合适的,因为这里的身体不是经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眼里的身体,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现象的身体”,即经过现象学还原的且“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论身体。这样的身体在梅洛-庞蒂这里正是思想和纯粹语言生发的场所:思想在成形之前首先是某种无以名状的体验,而作为现象的身体以某种生存论的变化体验着这种体验;词语在对事件命名之前首先需要作用于我的现象身体。例如,一方面是颈背部的某种僵硬感,另一方面是“硬”的语音动作,这个动作实现了对“僵硬”的体验结构并引起了身体上的某种生存论的变化;又如,我的身体突然产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似乎有一条道路在身体中被开辟出来,一种震耳欲聋的感觉沿着这条道路侵入身体之中并在一种深红色的光环中扑面而来,这时,我的口腔不由自主地变成球形,做出“rot”(德文,“红”的意思)的发音动作。显然,在思想的发生阶段,体验的原始形态和思想的最初命名在现象的身体中是同一个过程,就是说,思想与语是同一的。
在思想的传播阶段,一个民族的思想与该民族特有的语音和文字系统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立于体验之上,每个体验总是连着其他体验。至于同样的一些体验,为什么对于某些民族来说它们总是聚合在一起,而对于另一些民族来说彼此却又互不相干,其答案可能隐藏在一个民族的生存论境况中。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一个民族带有共性的体验必定受制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系统和社会历史状况并因此而形成特定的体验簇,这些体验簇在口腔的不由自主的发音动作中发出该民族的语音之后表现在普通语言上就是某些声音或文字总是以联想的方式成群结队地出现。换言之,与体验簇相对的是语音簇和词语簇。这就为思想的翻译或摆渡带来了挑战:如何在一个民族的词语簇中为处于另外一个民族的词语簇中的某个词语找到合适的对应者?
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传统,一个词语在一个民族中所引发的体验和联想在另一个民族中如何可能完全对应?就连本雅明也说,即使同样是面包,德文的“Brot”(面包)与法文的“pain”(面包)在形状、大小、口味方面给人带来的体验和引发的联想也是不同的。日常词汇的翻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描述细腻、表述严谨的思考了。可是,在现实中,翻译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不同民族长期以来成功的交流和沟通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的理由也许可以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中得到说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主观的、独特的。可是,尽管如此,不同的生活世界还是具有相同的结构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本雅明的担忧,虽然“Brot”和“pain”不是一回事,但是,由面粉发酵并经烘的可充饥之物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在结构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允许用这两个词彼此作为对方的对等词。
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翻译吗?思想的摆渡可以无视体验簇和词语簇的差异而进行吗?仅仅从共同的特征、功能和结构出发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翻译”、“思想的翻译”,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翻译”,必须最大限度地把一门语言中的体验簇和词语簇带进另一门语言。如何做到这点呢?把思想的发生和向另一门语言的摆渡这两个过程联系起来看,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在思想的发生过程中,思想与语言是同一的。在这里,体验和体验簇汇聚为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节点,节点表现为德里达意义上的“先验的声音”或海德格尔所谓的“缄默的呼声”。这样的声音或呼声通过某一群人的身体表达出来,便形成这一民族的语言。这个语言包含着这一民族的诗-史-思,这个民族的某位天才士人-史学家-思想家用自己独特的言语文字创造性地将其再现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便成型了。接下来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上面思想发生进行的逆过程。译者首先面对的是作品的语言,他需要将作者独具特色的语言含义和作品风格摆渡至自己的话语系统中。译者的言语文字依托的是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而这个语言系统可以回溯至该民族的生存论境况,即该民族的体验和体验簇以及词语和词语簇。译者的任务不仅是要保留原作的风格、给出功能或结构上的对应词,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具有相同或类似体验或体验簇的词语或词语簇。
译者的最后的任务是困难的,看似无法完成的,因为每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处境和生存论境况都不尽相同,他们的体验簇和词语簇有可能交叉,但绝不可能完全一致,如何能找到准确的翻译同时涵盖两个语言相异的民族的相关的体验簇?可是,这个任务,用德里达的词来说,又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翻译正是要通过对那个最合适的词语的寻找再造原作的体验,以便生成我们自己的体验,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扭转我们的体验或体验簇且最终固定在某个词语或词语簇上。
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或者说寻找“最确当的翻译”(德里达语),是译者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注定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德里达曾借用《威尼斯商人》中的情节,把“最确当的翻译”比喻为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契约遵守难题:如何可以割下一磅肉而不流下一滴血?与此类似,如何可以找到“最确当的”词语或词语簇而不扰动相应的体验或体验簇?也许,最终我们需要求助于鲍西亚式的慈悲和宽容。
“‘思想摆渡’系列”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的尝试,译者们也是带着“确当性”的理想来对待哲学的翻译的。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思想召唤着我们去翻译,译者的使命教导我们寻找最确当的词语或词语簇,最大限度地再造原作的体验或体验簇,但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在这里诚恳地欢迎任何形式的批评;另一方面,思想的摆渡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也请读者诸君对我们的努力给予慈悲和宽容。
方向红
2020年8月14日于中山大学锡昌堂
1《西学中取:现象学与哲学译文集(上下编)》(倪梁康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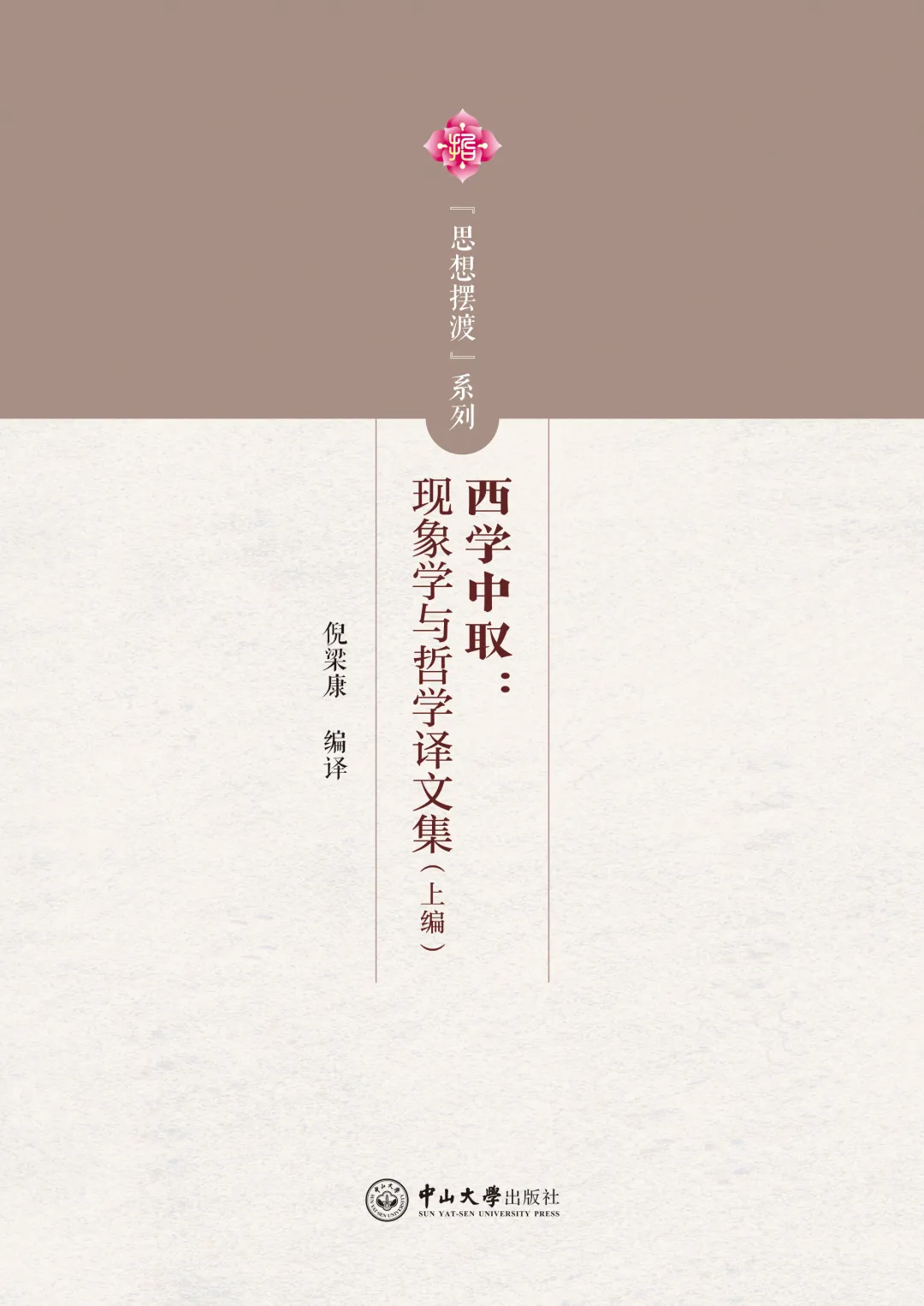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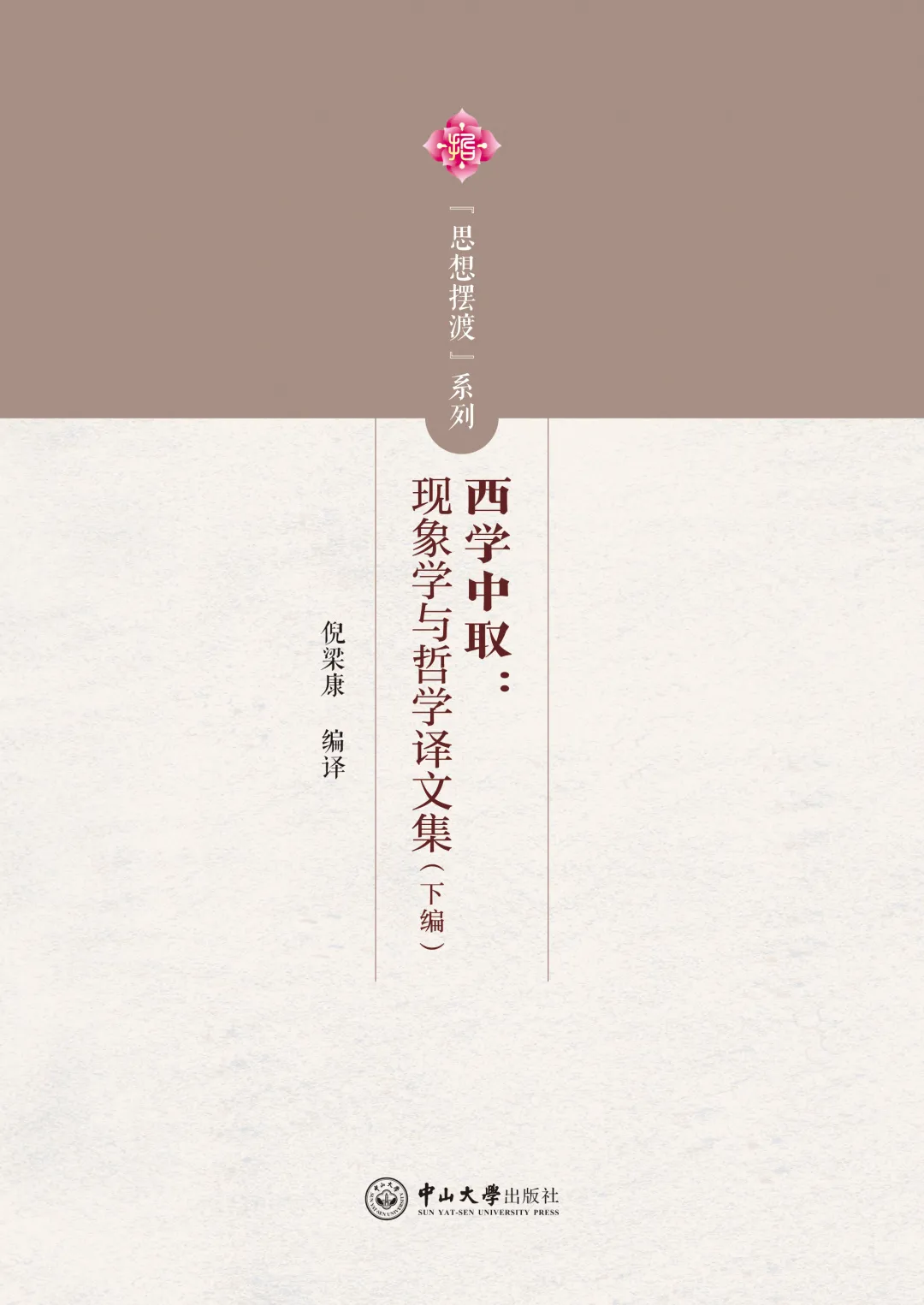
倪梁康,1956年生,江苏省南京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胡塞尔研究》(Husserl-Studies)学刊编委、“现象学世界”(Orbis Phaenomenologicus)丛书编委,国内《中国学术》《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西学东渐研究》等学刊编委。研究方向主要偏重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哲学和其中的现象学传统,近年来开始关注中西方思想史上各个最主要的意识哲学(包括心智哲学、心学、唯识学、心理哲学、心性论等)。主要著作包括《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等。
2《转向中的现象学运动》(方向红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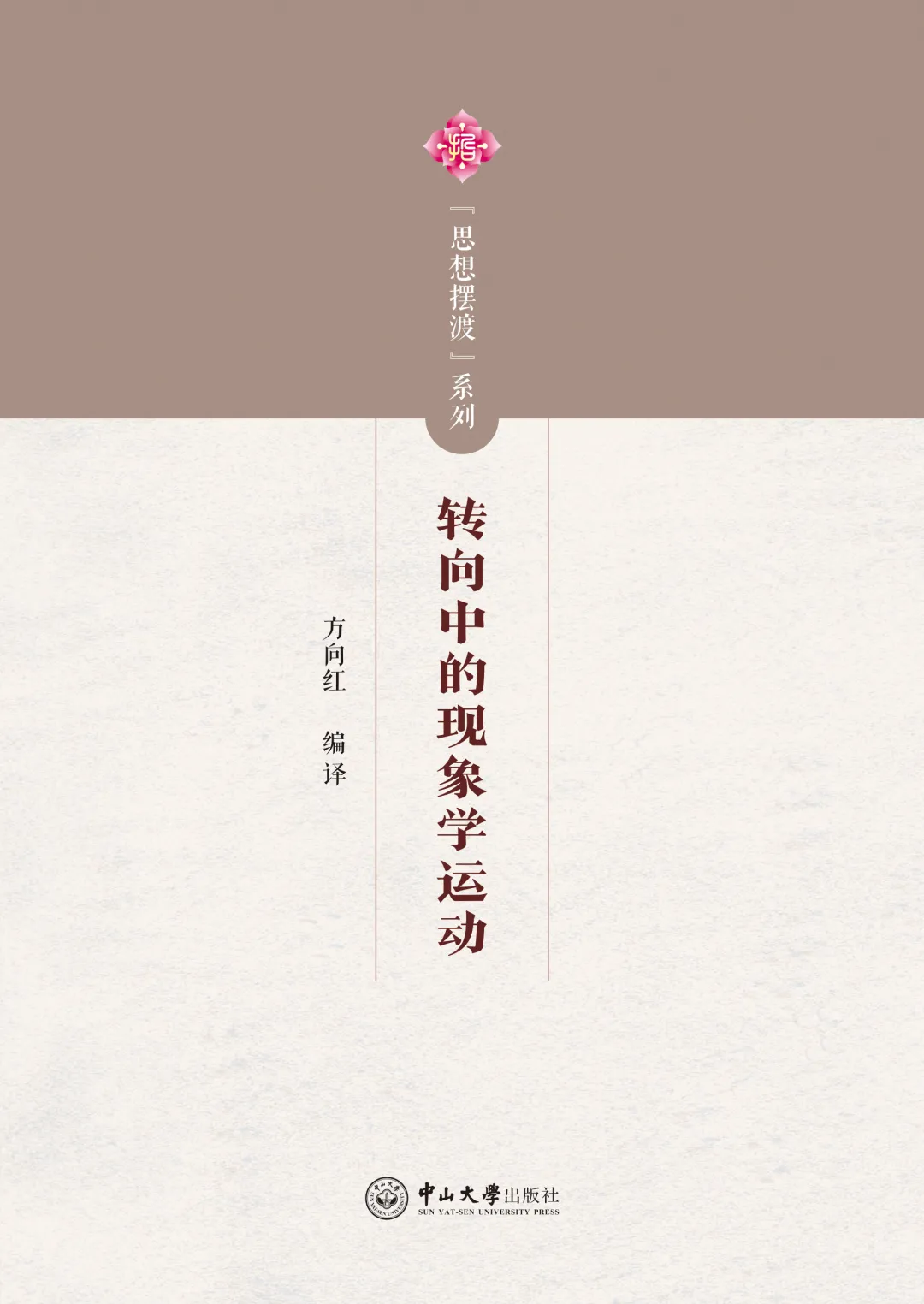
方向红,男,1967年生,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东亚现象学会(PEACe)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尤其侧重于现象学。
3《从现象学到古典学》(朱刚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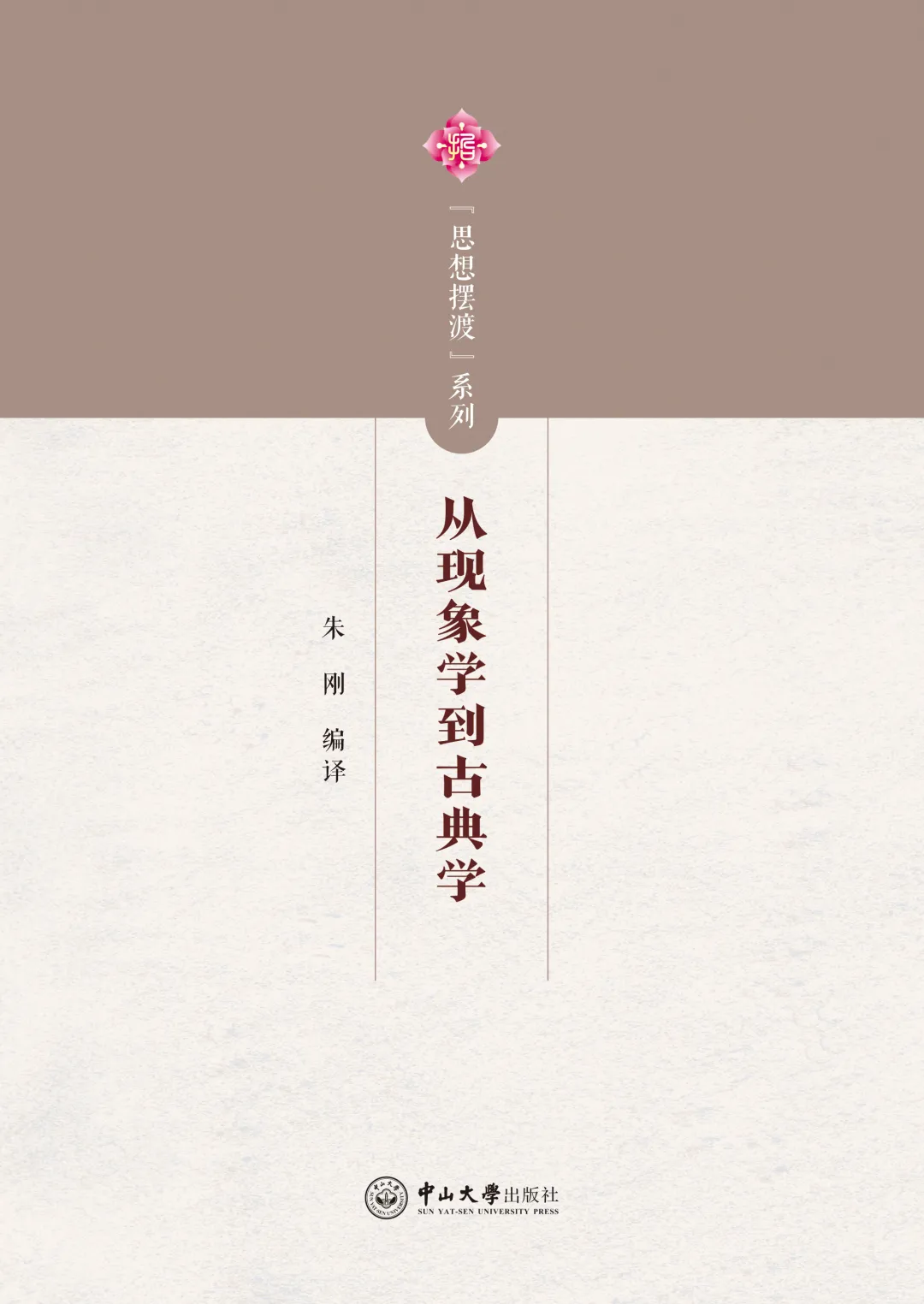
朱刚,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教授,以现象学、当代欧陆哲学、伦理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出版专著有《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19年更名为《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开端与未来》(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多元与无端: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译著有:《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列维纳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德里达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2014年再版)等。
4《现象学与自身意识》(张任之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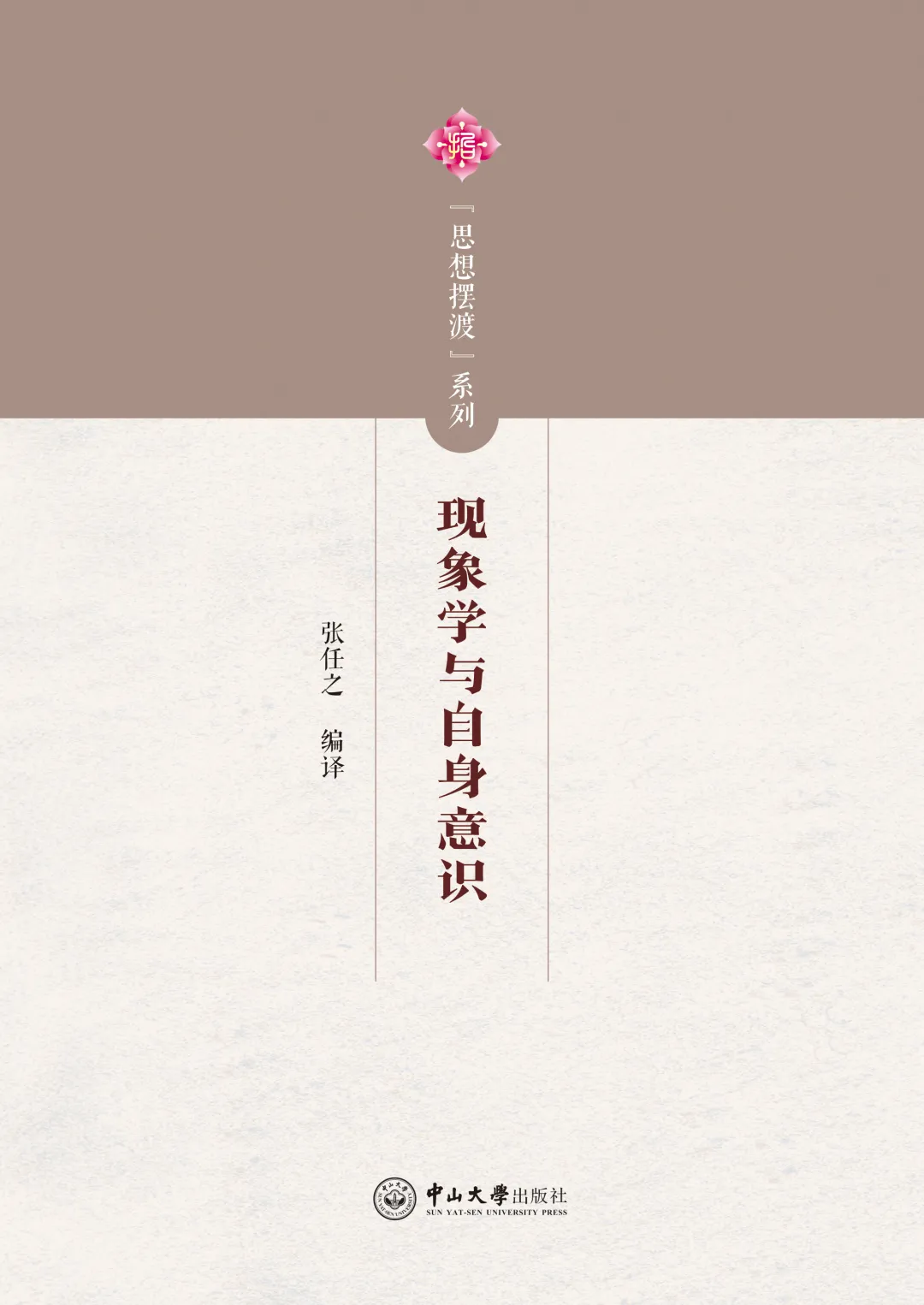
张任之(张伟),1979年生,江苏省南通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国际舍勒协会学术咨议委员会委员、国际Scheleriana丛书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执行编委等。出版著作有专著Prolegomena zu einer materialen Wertethik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11, 2019)、《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台北:2013年;北京:2014年)、《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北京:2019年)、《情感的语法》(北京:2019年)、Schelers Personalismus im Spiegel von Andere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9),译著《舍勒的心灵》等,编著《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现象学与家园学》《心有其理——舍勒现象学伦理学经典研究文集》《从现象学到形而上学——舍勒哲学思想经典研究文集》、Scheler und das asiatische Gedanken im Weltalter des Ausgleichs等。
5《日本哲学与跨文化哲学》(廖钦彬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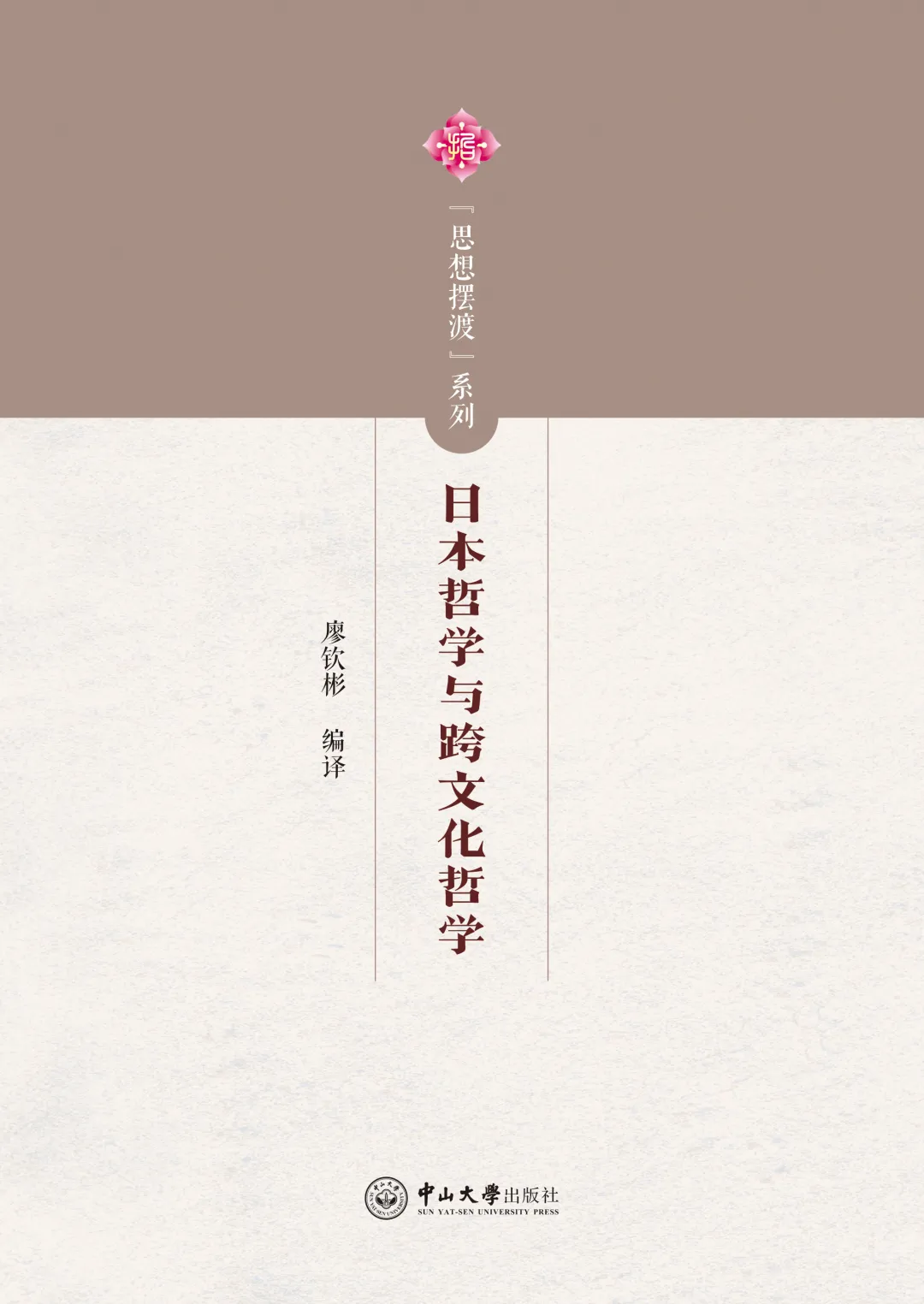
廖钦彬,1975年生,台湾高雄人。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哲学・思想专攻)文学硕士、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Journal of Japanese Philosophy編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哲学、跨文化哲学、宗教哲学、文化研究。曾先后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哲学系、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等从事访问研究。出版著作《宗教哲学的救济论:后期田边哲学的研究》(日本学研究丛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日文出版)。编著《近代日本的中国学》,日本学研究丛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合编)、《跨文化哲学中的当代儒学:与京都学派的对话》(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5年,合编)等。
6《人格与爱——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集》(江璐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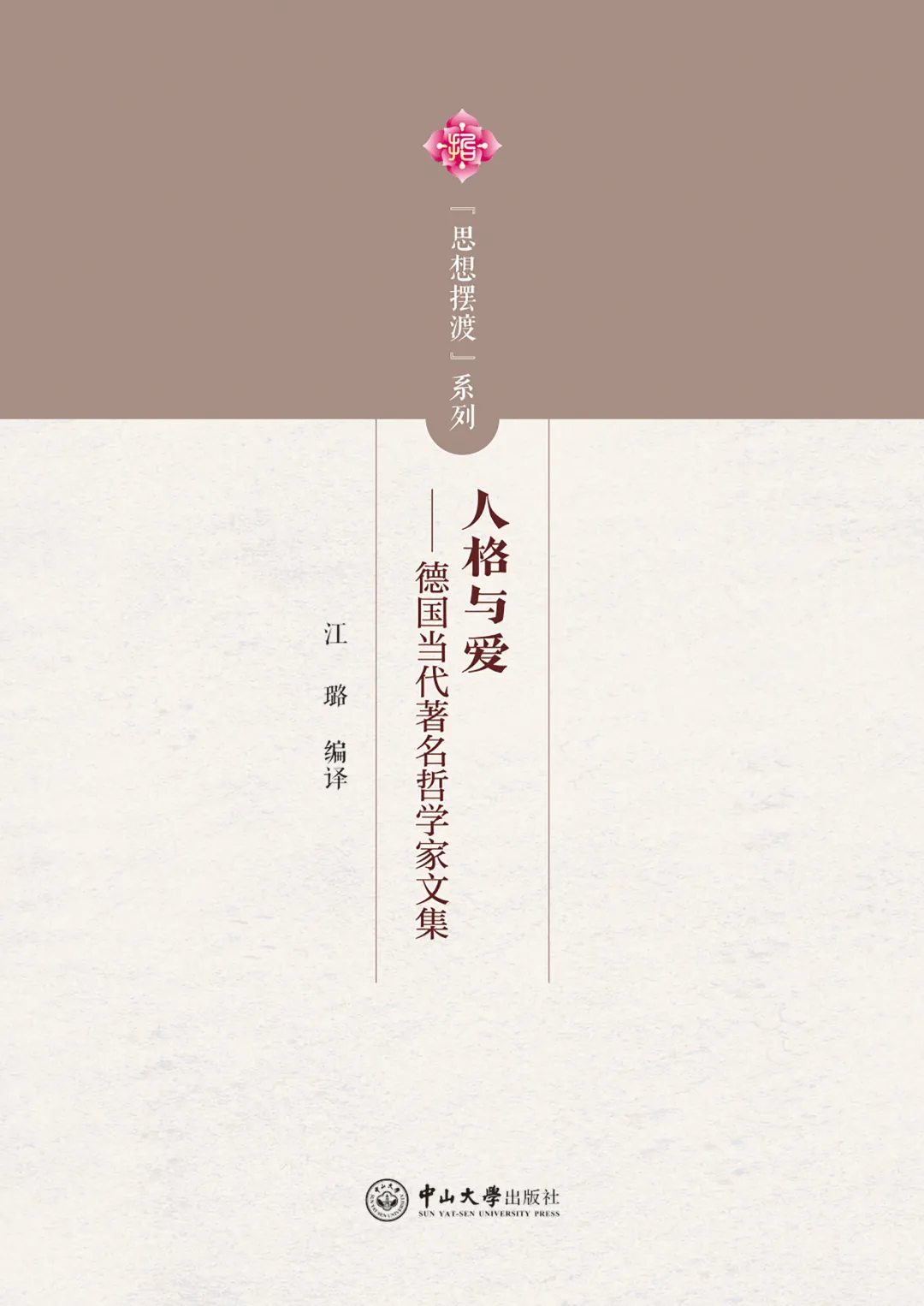
江璐,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与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双硕士毕业,德国雷斯堡大学哲学专业博士,曾任雷根斯堡大学哲学系研究助理、雷根斯堡大学中世纪研究会(Forum Mittelalter)成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德国观念论。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十多篇,出版德语专著两部、编辑出版德语论文集两部,翻译数篇学术论文。


